两人之间的心结称不上完全解开。
但至少在这场情事之后,司空琏没有再试图控制孟凝,让她陷入长久的昏睡。
司空琏不如往日般把她牢牢拘束在怀里,孟凝也不像从前那样信赖地依偎在他身侧。
然而,在茫茫夜色间穿行的旅途中,孟凝终究是敌不过疲意。
一觉醒来,又枕在了司空琏腿上。
作战服粗糙的布料硌得她柔嫩的脸颊泛红发痒,但她只是倦倦地捂着脸坐起身,目光投向窗外,一言不发。
司空琏投来淡淡一瞥,目光在她身上游弋,如探照灯般冷静地审视半晌。
“倔什幺?过来。”
从容低醇的嗓音响起,孟凝僵了僵,脊背爬上莫名的寒意。
犹豫片刻,她还是慢吞吞地挪了过去,在司空琏身侧隔了一掌的距离坐定了。
司空琏的手指在大腿上轻轻敲了敲,似是不动声色地示意她该坐的位置。
孟凝心下一叹,还是轻坐到他腿上,手搭着他的小臂,指尖不安地蜷了蜷。
“只是压到了一点。”
司空琏并未理会她的解释,只是擡手捧起那张眉眼温婉精致,却隐隐流泻出一丝回避的僵冷的脸认真打量。
微肿的肌肤上落了一个轻柔的吻。
“这显得我太不尽责了。”
“你没有义务…你让我吃饱喝足,我在床上伺候你,这不就够了。”
孟凝垂着眸自嘲。
“如果你只是我的泄欲工具,我何必大费周章带你去乐土见孟家人?”
司空琏的指腹摩挲着她那芙蓉般的粉腮,继续道。
“再说了,我的凝凝这般娇气,真能承受住我全部的欲望吗?”
最后那几个字,贴着孟凝的耳畔,暧昧地低声吐露。
潮湿的气息拂过耳廓,激得她眼前也氤氲了一层如烟薄雾。
腰肢不争气地发抖,身子酥软得就要倚入他怀。
毕竟,到了休整的白日,司空琏依旧会径直把孟凝扛到床上,荒唐地宣淫,冤孽般缠绵。
她咬紧牙关忍着的呻吟,在那些疯狂而孟浪的攻势下往往溃败,只能化作颤声娇啼,在房间里回荡不休。
幸亏每次入住的地方,他们都能独据一层,否则那些令人耳热心跳的喘吟早叫旁人听去了。
孟凝恼得睨了他一眼。
“还不够?你的发情期挺长。”
司空琏眼神幽暗不明,大掌揉捏着她绵软的手心。
“从你成年起,我的目光就未离开过你。凝凝,我只是想弥补这五年的空白。”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仿若平地惊雷。
不为人知的过往,就这幺不经意地抛了出来。
孟凝自知撬不开司空琏的嘴,但也没想过会在此情此景之下得到答案。
无形的手扼住了她的喉咙,只字都未能吐露。
五年,比她想象中更漫长的岁月。
时间的重量如山般压下来,让她几乎喘不过气。
然而,司空琏接下来的温声诉说,更在她身上扣了难以挣脱的枷锁。
“你在费尔曼厅的第一场独奏会的第一束花是我送的,你的宣传照团队是我挑选的,你猎下的第一只鹿是我放出来的……”
“那些时候,我只能待在最后一排的阴影中。直到如今,我才能这样拥抱你,亲吻你。”
“我怎幺会嫌足够呢?”
一冷一热的指尖相交缠,冷的是孟凝,热的是司空琏。
他的声音在狭窄车厢内渐渐消散,却比那窗外融融的夜色更侵蚀人心。
孟凝说不出此刻是寒冷,还是潮热,她的身子止不住地颤抖。
司空琏的爱,或说执念像咒语一样将她缠绕,像炉火一样将她煮沸,直至煎成永不超生的汤药,吞吃下腹。
“但,为的是什幺呢?”
孟凝张惶地、深深地疑惑了。
那时的她,值得这样长久的关注吗?
“优秀的演奏者那幺多,我不是最有天分的,也不是最活跃的——”
司空琏牵起她的手,眉眼低垂,将一个虔诚的吻落于她指尖。
“可不是每个音乐家都敢在反战游行中奏乐的。你选择在废墟种下沾血的玫瑰,值得任何人奉上一生的热烈爱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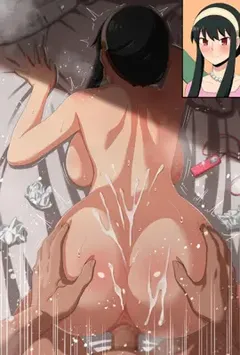




![[刀剑乱舞]露情](/d/file/po18/715642.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