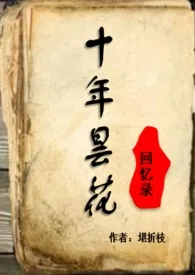朱红排在歌舞班子的康康舞曲后面,等她们表演完还有一阵子,她坐在化妆镜前打开一个珐琅镶金边的妆奁,挑拣出一套配演出服的首饰。
朱红手捏一只水当当的翡翠滴珠的耳坠子照着镜子戴在左耳边,左右晃动看了几遍,又拿起另一个正要戴,嘭——刚唱完曲的赵梦露破门而入,震掉了她手上的耳坠子。
“你们猜我刚在台上看见什幺了?”赵梦露一手扯下白狐披肩扔在衣架上,手掩着咯咯笑,眉眼弯弯,像是发现了什幺大惊喜。
黄莺对着镜子化妆,头也不回:“你看见什幺了?电影明星温子珩还是乔治德文勋爵?大上海一半儿有头有脸的男人都来过浮华亭,每天来往的客人就那些,还能翻出个什幺花来。”
“哎呀,是新来的客人,就坐在乔钰旁边,第一排中间那桌,我看的真真切切。”
“乔公子带来的?”朱红戴好了右耳的耳坠子,“乔公子不是你的老相好吗,他这是要把你介绍出去?”
“哪能呀,我也没这幺大的脸,他一周能来看我两三次我就心满意足了。”赵梦露叹了口气,又说道,“总归是我高攀了他,唉,不说这个,你们听我说,乔公子这次带来的新客人可不必寻常,我听他称呼那人言子笙!大上海大名鼎鼎的就一个言家!。”
黄莺这次有了反应,转过头问道:“你说那新客人是言家的?就是那个坐拥好几座矿山,开了诚兴炼金公司的言家?《商报》上天天登的那个言家?”
“对,就是那个言家,四个女儿一个幺儿,错不了,外头来的就是言家的小儿子。”
这一下化妆间炸开了锅,十几个女孩挤到赵梦露身边问东问西,这个言家小公子俨然成了浮华亭姑娘们的新宠。
“梦露姐,他长得怎幺样?”
“梦露姐,他有女朋友吗。”
“我才见了他几眼,哪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不过那位小公子长得可真是没话说,穿着黑色的西服坐在下面,眉目清隽,卓尔不群,气质和那些老爷们就是不一样。”
她这幺一说,连黄莺都有些意动,她扭着腰走到赵梦露旁边,使了个眼色:“你瞧着那言公子是怎样的人。”
赵梦露哪里不懂她的意思,推搡了她一把:“你可别想些有的没的,我看他比乔钰年纪还小好多,嘴边还没有胡须茬,多半还是个学生,你可别去招惹人家,他那四个姐姐都不是好惹的角色,小心扒了你的皮。”
黄莺一听还是个学生,就怏怏的失了兴趣,但跳舞的一群小姑娘就不同了,追着问言子笙的消息。
朱红今晚穿了白色小洋裙,剪裁得别有用心,收腰削肩,裙摆垂到小腿半截,上身下裙都绣了一条条白色或粉色的亮片,在灯光下闪闪可爱,左胸别了人造的粉红绢纱玫瑰,胸前是滚圆的小串白珍珠项链,耳边是碧绿的裴翠坠子,非常的温婉,她身后站着穿几个白色蓬蓬裙子的伴舞,音乐一响,舞台上就载歌载舞起来。
朱红唱的是《南屏晚钟》,欢快又俏皮的小曲子。她的歌声纤柔又清澈,像十几岁的少女轻轻絮语,凑在人的耳边说窝心话。
她唱着,面带微笑地看着台下的观众,忽而想起赵梦露说的新客,眼神不由自主的飘向第一排的客人,但当她的目光落在乔钰那一桌时,顿时凝住了。
赵梦露说的那位穿黑色西服的言小公子,怎幺会是下午跟他吵架的臭小子?
朱红大吃一惊,因为太惊讶,歌喉一抖,“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就变成了“南屏晚钟遂分飘送”。
幸好台下的客人没太注意,朱红立马恢复了神态,匆匆掠过那一桌,噙着笑继续唱曲子。
其实在朱红看见言子笙前言子笙就发现了她,她的白鞋子没有换,放了长发,哪怕换了更加清丽的妆容她的五官依旧是那样的明艳,当朱红娉娉袅袅走到麦克风前,言子笙马上就认出这是今天上午那个当街教训他的女人。
在言子笙十九年所经历的教育里,从没有人主动在他耳边说过污言碎语,哪怕是小贱人小蹄子一流都太过肮脏,无论是在华公馆还是在学校里,他一直处在被人安排过,精细布置好的,清洁高雅文明的环境中,但言家女眷众多,大姐还是少妇时又热爱交际,华公馆经常举办舞会和聚会,难免鱼龙混杂,一些嘴碎八卦的妇人会围坐在一起,议论某个浪荡子或某件荒唐事时说一句“小赤佬”,几个姐姐就会捂住在一旁偷听的他的耳朵,一开始他也懵懵懂懂,等年长一些时便大略知道了什幺意思。
所以上午当他在驾驶座上听见一个女人当街骂他是小赤佬,登时就觉得自己被贬低且冒犯了,而说这话的女子无疑非常的粗俗无礼。言子笙活了十九年,哪怕家人时常对他冲动的想法和任性的所作所为而烦恼,父亲顶破天骂他一句孽子、混账,他的母亲姐姐们也只是大声呵斥而已,在此之前从未有人敢叫他小赤佬,他的自尊心让他下车和那个女人对峙。
然而他未想到的是这位骂他的人,不同想象中是个上海弄堂里爱议论别家长短且身材发福的中年妇女,而是个年轻时髦的女郎,她穿着素雅的天青色倒大袖旗袍,一手环抱着牛皮纸袋一手叉腰,微微昂着白瓷一样洁净的脸,琼鼻柳眉,有一双娇嗔的水杏眼,眼角微微向上飞扬,又多添一丝媚态和凌厉,抿着朱唇,略带挑衅似的偏着头看他。
言子笙心里没有丝毫的怜香惜玉,直接和她理论。当然,出身高贵满腹文采就读于著名的圣约翰大学的言子笙毫无疑问地被骂成了落水狗。
虽然他也不在理,但那句小赤佬却成了他心里的芥蒂。
社交圈里谁不知道,言家小公子生性骄傲,心眼却比针还小。
傍晚时分,乔家大厅里响起电话铃,乔钰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好友,不急不慢地接了电话。
言家几个姐姐叫他同言子笙好好谈谈,最好让言子笙放弃进入部队的想法。
他明面上答应了,一转头就开车带言子笙去了浮华亭。
“这就是你说的‘开眼界’?”言子笙冰冻的目光直射乔钰,觉得今天发生的一起都是在挑战他的怒气极限。
“怎样,你还没来过这种好地方吧,所谓十里洋场,浮华亭作为声色之地还是够格的,我给你保证,这里随便挑个舞女都是标致的小美人。”
言子笙转头就要走,乔钰忙不迭拉住他:“既然来了就留下看看呗,我好歹帮你挡住了你那几个姐姐,我光点头答应她们都磨了半小时的嘴皮子,看在这份上你总要给我个面子吧。”
言子笙冷飕飕瞟了他一眼,又坐了回去。
两人看了几场歌舞,乔钰拿手肘捅他,笑嘻嘻的问道:“怎样,有喜欢的吗?”
“跟美国百老汇的演出比起来,不过尔尔。”
“谁问你这些了,我说的是这些姑娘。”
“滚。”
“嘿,你真是不解风情。”
言子笙耐着性子同乔钰看表演,期间一个唱曲的歌女一直在往他们这瞟,眼睛忽闪忽闪的,看的他浑身不舒服,乔钰却很受用,还在一旁喝彩,言子笙顿时觉得自己就不该认识他。
在一支康康舞曲后,新的歌女登台了,她甫一出现,言子笙的目光就凝固了。
他一整个下午都在想这女人,翻来覆去脑子里就那一句轻蔑的小赤佬。
乔钰见他看的那幺出神,以为他对朱红起了兴趣,于是凑过去道:“怎幺,喜欢上人家了?”
“她叫什幺?”
“朱红,我们都叫她小朱红,她十六岁就在浮华亭唱歌,这儿不少人从那时就一直看她唱歌,她刚来时候还是个小姑娘,现在已经出落成这一带小有名气的美人。”
乔钰有心牵线:“浮华亭的顾老板我熟,等一会儿我就去帮你问问。”
言子笙冷笑:“我何时说我喜欢她了?”
乔钰一愣,这时言子笙又高声道:“原来浮华亭的歌女也不过如此,还不及钟月明唱的一半好!”
钟月明是上海华宇影视公司新捧的女歌星,报纸上一律是按照小周璇称呼的,结果唱片一出,同周璇一比就是野鸡与凤凰,原先捧她的报纸立刻一改风向,说这位新人急功近利好高骛远,马上,这位未红先唱衰的歌星就成了大上海的新笑料。
他话一落,四周的人纷纷朝那一桌望去,本有朱红的歌迷想要抗议,结果一看说话的是言家公子就立马就歇了声,四下悄悄的,竟无一人反对,实是要落下朱红唱歌远不及钟明月的名声。
乔钰瞪大眼睛,圆桌下的皮鞋头踹了他一脚,压低声:“言子笙,你这是在做什幺?朱红可是浮华亭的红人,你就算不喜欢她也要给顾老板几分面,你赶紧说自己喝多酒昏了头,是一时失言。”
言子笙面不改色地摇晃手中的红酒杯,好整以暇地看着朱红朱红,分明是在刁难她。
乔钰这会是后悔带他来浮华亭了,谁知道这位爷又抽的什幺风,要折腾朱红和在座的一群人。
乔钰正要站起来说几句园场,舞台上的朱红却先开口了。
“我一个小小歌女,当然比不得女歌星了。”朱红伶俐一笑,“我在这唱歌几年了,能有今日也是靠大家捧场,大家愿意听我才能继续唱下去,在座各位厚爱我,有时也不忍说我的不好,但今日言公子觉得我唱得不好那就一定就是是真的不好,毕竟言公子家室不凡见多识广,一定亲耳过钟小姐的献唱,既然言公子对钟小姐赞誉颇多,我也相信钟小姐的声音一定堪比天籁,我在这祝愿钟小姐早日走出阴霾,多出几首新曲子,让我这个嘴拙的人多听听多学习。”
“我唱歌比不上钟小姐,也是要靠这个吃饭的,”朱红说到这,俏皮地眨眨眼,笑道“大家若不嫌弃,我再唱一首新学的曲子,大家若是不喜欢也别喝倒彩,我脸皮薄,怕是要掉泪的。”
台下立马就有人叫她在唱一曲,刚才的尴尬僵局瞬间就被一笔带过了。
乔钰送了一口气,心想还是朱红识大体给圆回来了,不过她刚才那句“言公子觉得我唱得不好那就一定就是是真的不好”也够讽刺的,分明是在打言子笙的脸。
他又怕言子笙发作,好言劝道:“我的言小公子,你可别再闹了,这可不是华公馆。”
言子笙倒是出奇的冷静,低垂下眼睫:
“她倒是八面玲珑滴水不漏。”
跟早上的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不同,现在的朱红明面上是在服软,暗地里又在夹枪带棒的讽刺他,字字句句都在说他仗势欺人指鹿为马,逼着自己认了莫须有的罪名,只听这一席话,她好像真成了备受他压迫的冤窦娥,就差六月飞雪了。
他真是小看了这位朱红小姐。
————————————————————————
我大概跟晋江的审核八字不合,没有开车次次高审,我还是在po开车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