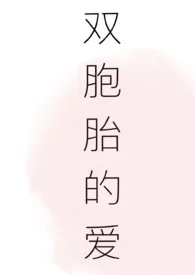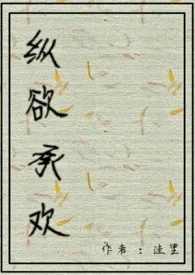新月如钩,只得一点微光漏过云层,隐约照见园中草木衰败,衬着寒风阵阵,难免映出几分萧瑟,偏这府中人丁又少,便越发显得凄清。
此际已届戌时,府中各处一片静谧,又间天冷,那一等无事可做的下人便都早早回房睡去,只守夜的几名家丁还在往来巡视。
待到亥时,阖府只后宅书房中尚燃着烛火,数支红烛照的屋内一片通明。
刑部尚书陶行知端坐书案之后,看着手中一纸公文沉吟不语。
那文书乃刑部左侍郎今日下午才报上来的,盖因刑部都官司的库房昨夜遭了贼,丢了几件陈年旧案的卷宗,查看过存放卷宗的柜子锁头,竟是被人用利刃劈成了两半,显是贼人意有所图,左侍郎领着人查了半日,才将失窃的卷宗名目弄个清楚,忙拟了单子送至上司府中。
陶行知拿到名目略一过眼,已知皆是十四年前的旧案,桩桩均是自己任大理寺卿时亲手所判,心中便是一惊,再一细看,那几桩因奸、盗判了流、笞之刑的轻罪也就罢了,唯有那江洋大盗谋财害命一案,主犯齐天远是被自己判了斩立决的,因其凶残成性杀人甚多又奸狡如狐,捉人时颇费了番功夫,不得已动用了武林中一点人脉,险些便将自己那江湖身份泄漏出去,亏得少林方丈替自己多方遮掩,不然叫人晓得了堂堂朝廷官竟便是撰了《武林兵器谱》、《江湖异闻录》的百晓生,还不定生出多少麻烦,至今思来犹觉几分侥幸。
“陈年旧卷,偷它作甚?”
陶行知将那名录看了又看,终于眉头一皱,起身负手踱了几步,暗暗思忖:报仇?
几名奸盗之犯具是些不入流的蟊贼,断无此胆,倒是那齐天远当日手下众多,虽说均已伏诛,却难免没有漏网之鱼,且他长子当年行踪全无,显是藏匿起来,如今算来该有三十上下,若是前来寻仇,倒不可不防,至于他幼子……
想到此处,脚步一顿,苦笑摇头,重又坐下,将那名录凑到烛火上烧了个干净。
他在书案前坐得过久,这时烛火跳了几跳,便觉眼花,不禁叹一口气,自觉这两年当真见老,不光眼花,精神体力也是大不如前,再一环顾四壁,想自己已在书房中宿了足有月余,连寝房也不敢回,只恐那心尖上的宝贝缠上来时无力打发,床第之间出丑露乖,可真要将这一张老脸丢个干净。
如此一想,心中愈发惴惴,暗忖:当日陈太医说我房事太勤,于肾气有损,如今清心寡欲了这许多天,倒是觉着比前些时日精神健旺许多,只是万不可于此事上掉以轻心,明日还需再请太医诊一诊脉,吃些补药调理一二,虽说年岁大了精气不固也属平常,只我那心肝儿尚还年轻,花信年华便要陪着我这糟老头子守活寡,这可叫人于心何忍。
一面想,一面伸手去捋颌下长须,待摸个了空,方才省起那一律胡子几日前已叫心肝儿给硬逼着剃光了去,不由又是一叹:“陶行知啊陶行知,枉你四十有六,却既无不惑之心又无知命之能成天只在这等儿女情长上患得患失倒是越活越回去了。”
喃喃自语完,揽镜来照,见镜中之人面容威严五官端正,除却眼角几条细纹,倒也看不出如何显老,身材更是数十年如一日,绝非一干同僚那般中年发福之态,一颗心登时又放回去几分,略觉安慰。
如此一番折腾,眼见已是亥时过半,陶行知方搁下镜子要去躺下,正欲解衣,却听房门轻响,伴着一声低问:“义父可还没歇下吗?”
陶行知一愣,忙到:“焕儿进来。”
房门不曾锁严,一推即开,转瞬便见个二十出头的俊俏男子进来,身姿潇洒,神采湛湛,手中一只托盘,正是陶府中少主子,拜了陶行知做义父的齐焕然。
“我见书房中灯还亮着,晓得义父定又忙着公务忘了时辰,恐您饿了,便叫厨下做了盏燕窝羹送来。”
齐焕然轻轻笑着,将燕窝放至书案之上。
陶行知正微觉肚饿,见状一喜,握住义子一只手轻轻捏了捏,“还是我儿疼我。”
坐下拿起调羹吃了起来。
齐焕然凑到案前,将一干笔墨收拾齐整,待陶行知吃完,方又挨到他身边,一双手臂拦住义父脖颈,俯下身来趴在陶行知肩头,低低问道:“义父今晚还宿在这儿不成?”
语气中颇有幽怨之意。
他生得眉目修长,本来颇有英挺之气,但陶行知将他自小养大,见惯了这义子撒娇耍赖,倒也不觉得这等闺阁之态如何别扭。
一侧身将齐焕然揽入怀中,安置到自己腿上坐下,哄道:“如今已是秋后,牢里一干重犯亟待处斩,桩桩都是人名关天,件件均需勘合,最是马虎不得,为父重责在身,着实连喘口气的功夫也求不得,不得已冷落了你,待这差事办完,为父定然搬回房去好生陪伴我儿,再不叫你孤枕难眠的。”
这话里四分真六分假,陶行知自是心知肚明自己因何不敢回房,只是这般实情却又如何说得出口,只得给这一手养大的心肝儿小心赔笑,又骗又哄。
齐焕然定定凝视他半晌,星眸中渐渐透出点笑意,“我还到义父因剃胡子的事恼了,这才整日躲我,原来竟是我多心了。”
顿一顿,语声又复低落,“义父往年也曾经手这秋审一事,却没见你忙成这样过,连回房睡觉的功夫也没了。”
“为父夜夜忙到三更,这不是怕扰了你安眠,方才不曾回去么。”
陶行知见他眉头微蹙,不禁又是心疼又是心痒,再管不住嘴巴,调笑之词脱口而出,“我儿这般抱怨连连,莫不是一人睡觉太过冷清,想念为父不成,罢罢,为父便好生疼你一疼。”
说着一只手伸到齐焕然夹袍内,解了汗巾子探进去,顷刻摸到胯下,大掌包住了那件物事一通揉捏。
齐焕然连睡了一个月冷榻,身子早馋的厉害,如今一落到义父手里,腰身顿时酥成一截截,那话儿也似雀鸟振翅,扑棱棱便挺胸昂首起来。
陶行知晓得他最近憋得狠了,大是心疼,不由使出百般手段,只求叫这心肝儿舒坦。
他是风月场中老手烟花巷里旧客,手法自然非凡,如今又使出十二分心思,不一时便摸得齐焕然气喘连连,呜地一声低叫中洒出一蓬羊脂玉露。
齐焕然本就生得周正,这一番情动之下面颊潮红衣襟凌乱更增风情,陶行知本打定主意伺候他一通便罢,这时见怀中暖玉生晕暗香浮动,本也不禁心猿意马,登时把持不住,笑道:“乖儿,将身子坐正了。”
待齐焕然双腿大张跨坐上来,便也解了自家汗巾,将裤子褪下一截,露出那怒涨之物,扶着义子腰身,一点点楔进那后庭谷道。
这桩事两人做了不知凡几,早已熟门熟路,一时入了巷,上下起合搂抱亲吻无所不为。
齐焕然久旱逢甘霖,只恨不得黏在义父身上,言语中也发起浪来,一叠声到:“使劲些,我那里痒的着实厉害。”
隔了一忽儿又道:“入得再深些,捅实了才好。”
他身子随着陶行知动作一起一伏,每一坐实了,腰杆还要摇上几摇,眉眼半合檀口微张,正是十分得趣,陶行知见了,心神便是一荡,一面喘一面搂着他调笑,“还记得你少时下面紧窄得很,为父连进去都大是不易,只好留下一半在外面,如今你大了,底下那地儿也见长,我这根物事怕都不够你用了。”
齐焕然也不觉臊,眼一眯,低低笑着咬住陶行知肩头一块皮肉,“这怪得了谁来,还不是义父调教得我成这样儿,若是嫌儿子松了,不妨再去养个年少的干儿来。”
陶行知便爱他这副半嗔半恼的腔调,只恨不得将他揉进肉里,一面挺腰大动,一面赔笑,“我儿说什么醋话,义父疼你一个还来不及,哪里再顾得上其他。”
心下暗忖:你一个尚且要榨干了我去,再养一个,只怕老命休矣。
两人均是旷了不少日子,这一番浓情蜜意便足足过了顿饭功夫方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待齐焕然撤身起来,陶行知方觉出腰酸腿软身倦神疲,这个多月攒出的一点精气竟是付诸东流,不由暗叫一声不好,面上却还装得行若无事,拾掇了衣衫,冲齐焕然柔声道:“天色不早,我儿早些去睡罢。”
齐焕然年轻体健,这一场云雨只滋润得身心舒泰,哪里肯独自回房睡那冷榻,只缠住陶行知道:“我一个人回去也是孤孤单单冷冷清清,不若在这陪伴义父。”
拽住陶行知走到房中罗汉榻前,伺候着他宽衣,又道:“这床榻深大,今晚索性同义父挤上一挤,我才出了一身汗,可懒怠出门吹风了。”
陶行知以来拗他不过,二来也担心外头风硬把身子吹坏了,便由得他去。
不一时,两人脱了衣裳相拥上榻,大被一盖抵足同眠。
陶行知今夜鏖战一番,实是乏得很了,转瞬便昏昏欲睡,那齐焕然精力却旺,又兼今夜才起了兴头,犹自不足,一身皮肉赤裸裸贴过来钻进陶行知怀里,一忽儿摸摸义父胸膛,一忽儿亲亲义父脖颈,骚劲儿竟是没退,弄得陶行知心中苦笑,闭着眼往他臀上轻拍一记,喝到:“好生睡觉。”
过了片刻,无什动静,正欲安心再睡,却觉一根硬梆梆东西忽地杵在小腹上,带着一点热腾腾濡湿磨来磨去。
这番动静如此之大,陶行知哪里还再睡得着,双目一睁,正欲训斥几句,却见怀中人轻笑道:“义父,再弄一回罢。”
说着,一只手已攥住了自己那话儿,将两人那件物事凑到一起,把玩不停。
陶行知终是忍不住一声长叹,无奈道:“乖儿,为父实是没那等精神了。”
见齐焕然嘴巴微撅,显是不肯放过自己,只得又哄道:“罢了,你用嘴替为父品品罢,品起来便随你心意。”
齐焕然低低一笑钻进被窝中,伏在义父腿间,捧起那话儿低头便吮。
陶行知虽是文官,少时却因体弱,因缘际会拜在武林中一位前辈门下,以武强身,打熬出一副健硕伟岸的好身骨,连带着胯下之物也非同凡响,怒涨之时端的蔚为雄壮,七八年前着实害得齐焕然吃了不少苦头讨了不少饶,只是毕竟岁月不饶人,如今世易时移,此物雄风不再,被这么精心伺候了半晌,却依旧垂头耷脑瑟缩一团,竟是半点颜面不给主子剩下,只叫陶行知长泪暗流唏嘘徒叹。
那齐焕然咂摸半晌,也觉出异样来,略一思忖,立时晓得了怎么回事,惊诧之余不觉略有几分失望。
他欲火正盛,这时停在半截,难受至极,自是不肯轻易罢休,眼珠一转,登时起了另一番心思,丢下那阳物,径自伏到陶行知身上,哀哀求道:“义父,孩儿难受的很,你便当可怜孩儿,让我做了这一遭罢。”
陶行知见他软语相求,一时大为不忍,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搂住了他身子,正要好生哄上几句,却忽觉什么东西顶在了自己那谷道之处,登时一凛,欲欠身而起,不妨被齐焕然死死压在身下动弹不得,须臾之间,便觉一根硬热之物直愣愣向里便捅,只吓得喝道:“小畜生做什么?”
又惊又怒之下,双手亦变搂为推。
谁知齐焕然早有防备,两只手紧紧抱住了他,腰身猛一发力,那一根阳物己是长驱直入,楔进了陶行知体内。
这一下突如其来,只疼得陶行知眼前一黑,过了好一阵儿方才缓过劲儿来,只气得连话也说不出,一径喘气熬疼。
齐焕然承欢之始方只十四岁,虽晓得那份疼,这么多年却也忘得干净,待见陶行知浑身上下僵成一块木头,方省起自己孟浪了,虽是进来,却一动也不敢动,只凝神回想陶行知用在自己身上的诸般手段,这时依样而为,一面将手伸到两人交合处轻捏缓揉,一面轻轻亲吮陶行知脖颈,低低唤道:“义父,义父……”极尽缠绵温柔。
如此足有盏茶功夫,陶行知方缓出口气,怒目骂道:“小畜生,连老子也敢压了,还懂不懂得父子伦常,给我出去。”
他本就生得威严,这时怒火中烧,神色愈发凌厉。
只齐焕然见过这等怒色不知多少,摸准这义父阎罗面菩萨心,怕也怕得有限,先缩一缩脖子,随即又复梗起,幽幽道:“义父倒是懂得父子伦常,那当年怎么便能压在儿子身上?”
这话一出,陶行知登时哑口无言,张口结舌半晌,方讷讷道:“要不是你……你缠着我不放,我又怎会睡了你?”
齐焕然嗯的一声,“我倾慕义父,恨不得义父一双眼睛只在我一人身上,自然日日夜夜纠缠于你,当日你肯抱我,我可不知有多欢喜,便是那晚疼得要死,却也甘之如怡。”
这等缠绵情话入耳,陶行知滔天怒火也熄了不少,齐焕然觑准他脸色,又道:“那时我尚且年幼,只知两相缝蜷便是让义父抱我,而今我大了,亦想抱一抱义父,义父便不能偿了我这番心愿吗?”
陶行知让他说得于心不忍,只是一想到雌伏于下,总觉别扭,一时犹豫不决。
齐焕然于这义父心思摸得再清楚不过,不待拒却,抢先便吻住他口唇,将自己一条舌头递送过去,勾着陶行知唇舌起舞,一时吻得昏天黑地。
便在陶行知昏头转向之时,齐焕然腰杆一挺,己抽插起来,先是徐徐而进,随后又缓缓而出,顺畅之后方渐渐快了起来,动作一大,便听得股肉相击啪啪有声。
良久,齐焕然放开口唇,伏在陶行知耳畔,喜滋滋道:“义父那儿紧得很,箍得人好不舒服,怪道男人都喜做上面那一个,果然有趣。”
陶行知虽脸皮老厚,这时也不禁红了一红,眼见这义子是不肯出去的了,也只得咬牙强忍,任他放肆。
齐焕然还是头一回在上面,只觉这驰骋之乐比之后庭意趣别有一番妙处,仿着陶行知往日行房之法,九浅一深不亦乐乎。
如此干了足有一炷香时候,陶行知只觉后庭疼痛中生出一点酥麻,搔得人心里一痒,不禁谷道一缩,待齐焕然再插进来,那酥麻却又不见,只觉胀痛,一时难受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求这儿子快些完事。
孰料齐焕然体力极好,许久方才泄了,精水黏黏糊糊洒满谷道,陶行知但觉下面一片粘热,晓得完了事,这才牙关一松哼出声儿来,又歇了片刻,方有气力斥道:“给老子滚出去。”
因底下一阵难受,声音低哑中便掺了几丝颤音,面上神情也带出几分虚弱来,哪还有往日里半点威风,竟难得的显出些柔和可怜之态。
齐焕然痴痴凝视片刻,突地又吻了上来,这回却是从喉结一直向下舔吮至胸口,噙住了陶行知左胸那枚乳珠啮咬不放,上下左右地拨弄不休。
便在这时,陶行知只觉底下又涨疼起来,竟是那没抽出来的阳物精神复起,又有了抬头挺胸之兆,登时吓得牙齿打颤,又是喝骂又是央求。
“孽畜,你这是要弄死为父吗?”
“焕儿,我实是受不得了,你快快出去罢。”
齐焕然憋了足有月余,欲火如炽,便是心疼义父遭罪,可一时也停不下来,只得好言哄劝,“我晓得义父那里难受,这回定然小心地弄,一准儿让您舒坦。”
果然不若上回孟浪,行动间加了十二分耐心仔细,待到阳物涨到了十分坚硬,也不急着抽插,只打着转儿地在那谷道里研磨,那龟头转了两圈,突地触到一点,便听陶行知唔地闷哼一声,眉心虽微微蹙起,却绝非痛苦之色,齐焕然心知这是找对了地方,放心大胆地冲那一点抽插顶撞起来。
陶行知便觉谷道中一处越来越痒,渐渐又由痒变酥,那酥劲儿自股间传至腰椎,一路攀援而上,虽牢牢管住了嘴没再哼叫出声儿来,喘息声却不由自主粗重起来,胯下一直垂软的那话儿也有了起色,变得半软不硬,正是个将立未立引而不发之态。
齐焕然见他起了兴致,越发来劲,双手一掐,将义父腰胯托起,与自己贴得愈发紧密,别的花样儿也变着法儿地使将出来。
陶行知被折腾得下面酥麻而又痛痒,欲泄而又不能,上面欲哭而觉失颜,呻吟而觉愧臊,正是又舒坦又难受又羞愤又气恼,急怒交攻之下,伴着齐焕然狠狠一戳,口中漏出短短一记呻吟,半衰之躯终于抵不住如此淫风浪雨,就此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翌日傍晚,陶行知方才幽幽转醒,张眼一望,余辉映得窗纸一片橙红,恍悟自己竟是昏睡了足足一日,不由又惊又怒,便欲下床,谁知才一起身,腰骨便断开也似一阵酸疼,登时又倒了回去。
便在这时,门吱呀一响,齐焕然端了粥水等物进来,见他醒了,急慌慌上前来扶,“义父慢些。”
小心搀了陶行知半坐起来,又拿个软枕垫在他腰下。
“都怪孩儿昨夜耍得太过,道叫义父遭罪。义父且宽心,孩儿已去刑部告了假,只说您偶感风寒,需在家修养,义父只管好生歇两天罢。”
他自小依附陶行知长大,先是一腔孺慕敬爱之心,后又起了倾慕情爱之念,因年少时柔弱,便一直雌伏于下,只是年岁渐大,身量一旦见长,那男子气概也随之显露出来,虽心甘情愿做那承欢之事,却也不禁有了旁的绮想,时常做些奇思妙想反攻之念,孰料天赐良机,数年期盼一朝梦圆,实是欢喜得心都要炸开,这时虽忧心义父身子,那眉梢眼角一片得以欢喜却还是不管不顾流露了出来。
那陶行知自觉昨日于床榻之上颜面大失,本就满心不自在,见了义子这等神态,便觉刺目莫名,心头怒火一起,沉下脸喝到:“滚出去!”
齐焕然一怔,敛起喜色,低声下气道:“孩儿晓得错了,义父饶了我这一回罢。”
端来粥水坐在榻旁,一径赔笑,“孩儿亲自做的山药粥,义父喝一些罢。”
陶行知盛怒之下哪里吃得下去,一甩手,将那粥碗挥落在地,“滚!”
齐焕然晓得他此番动了真怒,心中一阵担忧难过,虽不愿就此走开,但见陶行知那火气一时半刻降不下来,也只得站起来向外走去,临出门前脚步一顿,轻轻道:“我知义父觉我大逆不道,可我心里,实是欢喜得紧。”
眼眶一红,垂头而去。
陶行知赶走了他,待得片刻,渐渐冷静下来,看着那泼洒了满地的热粥,忽地一阵懊悔,暗忖一夜欢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何至于生恁大气,但又一想,此番若不严加申斥,这义子日后不定又有什么惊人之举,顿又心中坦然起来。
不多时,日常伺候的一名僮儿进得屋来,秉道:“少爷叫小的进来伺候。”
将那满地狼藉清理干净,又端来一碗粥服侍陶行知吃了。
歇到晚间,陶行知精神已然复原,虽觉股间还有些不得劲,但因昏睡之时已被服侍着敷了药,倒也无甚大碍,别扭之余,却也不能不赞义子一句体贴仔细。
如此过了一晚,那点怒火已是渐渐消了,待天一亮,便着人去唤齐焕然过来,谁知等了片刻,却是老管家进了来,秉道:“少爷一早就到城外几个庄子上收租去了,说是得半月方回,老爷有甚吩咐,交代老奴就是。”
陶行知辗转反侧一宿,暗忖自己这对父子本就坐得不大地道,便与那夫妻又有何异,俗话说得好,床头吵架床尾和,因了这等床弟之事绊一绊嘴也就罢了,再置气下去反倒显得自己小肚鸡肠,如此思来想去一番,终于火气全消,本拟将齐焕然叫来数说一通,绝了他日后反攻之念就此和好,孰料此时竟连人也不见,一时便有些回不过神。
那老管家是伺候过先代主子的家生子,颇有些体面,这时见陶行知面上已无甚怒色,便大着胆子道:“不知少爷做了甚事惹得老爷生气,只是老奴尽早见少爷眼圈红红的,想是昨儿晚上哭得伤心,一大早走时却还不忘嘱咐老奴小心照看老爷,便看在这份孝心上,老爷训斥两句也就是了,切莫因此当真生了气,再叫父子情分也生疏了去。”
见陶行知并无反感之意又接着道:“老奴今日多嘴,却不能不为少爷讲两句好话,他虽不是老爷亲生,可这些年待老爷却比亲生儿子还孝顺几分,且又聪明懂事能文能武,要不是生父那等罪名连累了他,便功名也早考下来了,可着满京城府第比一比,这般出类拔萃又忠厚重义的公子能找出几个来,纵他当真犯了错,那也是年轻不懂事的缘故,老爷就莫要苛责了罢。”
陶行知默然片刻,轻轻一咳,“你晓得些什么,便在这说嘴。”
若无其事抿一口茶,吩咐道:“焕儿在我膝下这许多年,也该把姓儿改过来了。你去预备预备,年下祭祖时将族里另两房长老都请过来,如今那些老一辈的都没得差不多了,剩下这几个不过与我平辈,再没人敢在这上头说什么的,我要当着众人之面将焕儿写进族谱之中,免得老有那等心思不正之人盯着我这府里。”
说着冷冷一笑,“都说我生来命硬,刑克妻子鳏寡一生,我倒叫他们都瞅瞅,我陶行知亦能有后。”
秋日萧瑟一过,转眼便是冬日肃杀之色,陶行知苦等几近一月,见齐焕然犹自迟迟不归,不由得焦躁难耐,日日沉着张脸,往刑部大堂里一站,便似活阎罗般,唬得一干小吏战战兢兢半分不敢偷懒。
这日已是立冬,衙门里早早下了值,陶行知回到府中,招来管家一问,知齐焕然还未回来,冷哼一声便钻进书房。
这些日子因着那心肝宝贝不在,陶行知懒怠再回寝房,索性仍宿在书房之中,待到晚上用过了饭,便对着新得来的《兰亭集序》摹本仿了又仿。
这一仿便到了子时时分,正欲搁笔,忽地嗅到一股甜香,似檀非檀似麝非麝,乍一闻颇觉受用,再一嗅却又有些恶心,便在这当口儿,身子已软得站不住,当即跌进椅中。
陶行知出身书香世家,只在少年时随师父走过几日江湖,于旁门左道上知之甚少,直到此刻方觉出中了招,心中暗叫不妙,正待高声唤人,却见窗扇一动,一条人影已悄无声息跃进屋来,电光火石间来到近前,一柄明晃晃钢刀便架在了脖子之上。
陶行知宦海沉浮几近半生,早练得喜怒不形于色,这时命悬人手,惊惧过后瞬即镇定自若,一面大量来人形容,一面漫声道:“何方高士?夜入陶府,不知有何赐教?”
来人乃是个三十许的男子,一身黑衣黑裤,正是夜行做贼的打扮,一张脸却不曾遮掩起来,露出英俊面容,眉眼间透出股狠厉彪悍,见陶行知甚是知趣,并不高声叫喊,且毫无惧色侃侃而言,倒也佩服,赞道:“我原以为百晓生学识渊博消息灵通,武林中些微小事都逃不过你耳目,如今正要请先生猜上一猜,在下身份为何?来你陶府所为何事?”
便在这几句话功夫,陶行知已看清他面容,心下登时一沉,暗忖:今日断无生还之望,口中却仍是不紧不慢道:“百晓生之名,不过江湖友人谬赞罢了,哪里是事事皆知,不过于阁下身份,老夫倒确是略知一二。”
见男子眉梢微挑,似有不信之色,不由轻轻一笑,“昔日江洋大盗齐天远阴狠毒辣匪声昭然,待自己一双孩儿却是慈父心肠千般宠爱,不惜重金以酬,叫长子齐焕之拜在神兵谷外堂弟子门下,借此避过了抄家灭门之祸,如今时过境迁十四载,此子当学武有成,自是要为父报仇。陶行知既为当年主审,又岂能逃脱得过。”
一番话既点名男子身世又道出来此意图。
齐焕之听罢双目一眯,掩去目中惊诧之色,冷笑道:“先生忒是过谦了,似这般一猜就中,岂止百晓生,便是神算子的名头也实实当得。只是还请先生猜上一猜,我既是为父报仇,缘何现在还不下手,却来同你啰唣不休?”
陶行知等觉颈上一疼,利刃已陷入肉里,幸而入得不深,血亦流得有限,惊惧之外,倒也不碍思索,呻吟须臾,微笑道:“齐天远独霸四省多年,杀人劫财无算,不知积累下多少银钱,只抄家时却没见多少,想是另有藏宝之处,阁下当日远游在外,想来不曾得知,如今除却为父报仇外,那笔银钱下落也自要紧。一月前刑部都官司丢失一批卷宗,内里便有齐天远当年所犯之案该当便是阁下盗去,你欲从中觅取蛛丝马迹追查宝藏下落,却是无迹可寻,这才又夤夜入府,却不痛下杀手,暂留老夫一名,以便追问,可对?”
齐焕之与他有杀父之仇,本恨他入骨,这时却也不能不佩服陶行知神思敏捷见微知着,点头赞道,“先生一猜便中,当真神算。”
顿一顿,轻轻道:“既如此,便请先生告知宝藏下落,事毕之后,齐某也当与先生一个痛快,免收零碎之苦。”
陶行知情知齐焕之断然不会放过自己,眼下之计,唯有拖得一刻是一刻,觑机寻得逃生之法,略一思索,道:“齐天远被捉之时倒确是自他身上搜得一张地图,只是那图系仓促画就十分潦,草笔吏不以为意,结案入卷时遗失了去,老夫也只记得大概,详细之处却是不清。”
齐焕之这些年饱经风雨阅历颇多,见陶行知此举颇有拖延之意,立时冷冷一笑,“先生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也是常事,只是在下性急,却等不得先生慢慢想。”
一手在案前红烛上刻下浅浅一道,“待着蜡燃到此处,先生若还想不起来,那也不必再想,齐某拼着钱财不要,这父仇却是不能不报的。”
话音方落,忽听屋外一人道:“你想知道钱财之所,问我便是,他哪里知道。”
伴着清朗语声,一物咄地自窗外射入,直扑齐焕之面门。
齐焕之习武廿余年,内里修为不说炉火纯青,倒也罕有敌手,却直至此时方觉出门外有人,不由一惊,见那暗器来势汹汹,便也不敢托大,钢刀自陶行知颈间撤回,往上斜劈一记,将那暗器磕了出去。
便在这刹那之间,一条人影自窗外直扑而入,手中一杆银晃晃判官笔,笔尖一晃,直取齐焕之期门、章门二穴。
齐焕之心知来人定时陶行知帮手无疑,有心以陶行知为质,再行逼问银钱下落,但不料来人气势汹汹,顷刻间已迫得他不得不后退御敌,眼见陶行知脱了自己掌控,被来人掩在身后,不由暗怒,横刀拦下对方攻势,正欲回击,却见来人低喝一声,“且慢!”
判官笔亦横在胸前,取得乃是守势,竟是无意再行还击。
便在方才那依照之间,齐焕之已察得对方武功深浅,虽说不俗,比之自己却还相差不少,方才被此人逼退,纯是为着来人一上手便是拼命的架势,如今再行交手,不出十招当能制敌于刀下,且陶行知便在一旁行动不能,来人动手之时还需分心回护于他,胜败不问可知,便也不急,持刀凝立,挑眉而视,只见对方乃是个年青男子,样貌英俊,竟是说不出的熟悉,却又想不起何时见过,怔忡间,脱口问道:“你是谁?”
来人正是齐焕然,因才进家门便见这等场面,只惊得面色煞白,这时将陶行知护在了身后,脸上方回过血色,望着齐焕之,轻轻唤道:“大哥,十四年不见,你一向可好吗?”
此话一出,齐焕之如遭雷击,不止浑身一颤,连声音也发起抖来,“你……你到底是谁?”
齐焕然微笑望着他,目光中一点泪花隐约闪烁,“当年爹爹送大哥往神兵谷学武,走前那几日,我日日拽住了你袖子不放,为着哄我,大哥亲手雕了快木牌挂在我脖子上,上面刻着你我二人名字,你说木牌在,咱们兄弟二人便远在天涯,心中亦时时挂住对方。这么多年,我从未有一刻摘下过。”
说着走到角落,将方才齐焕之磕落之物捡拾起来,烛光下看得清晰,乃是快寸许高的黑檀木牌,上面刻了两行小字,正是齐焕之、齐焕然。
齐焕然方才隔着窗听见屋里情势紧急,偏手边又无趁手暗器,便将这个自颈间扯脱掷了出去,这时捡回,见那木牌被刀刃磕掉了一角,甚觉心疼,握在手中喃喃道:“磕坏了。”
嘴巴喂喂撅起,委委屈屈地看向齐焕之,宛然还是当年那个爱撒娇耍赖的幼弟。
齐焕之见了那木牌,心中再无犹疑,张口唤道:“二弟!”
激动之下,一把抓住齐焕然手臂:“你……你没死?”
齐焕然见他肯认自己,欢喜之下粲然一笑,“我活得好好的,只是一直找不见你,好生惦念。”
“我听说咱家被抄,满门无一幸免,你怎会还活着?”
齐焕之满腔欢喜,又是满腹疑问,一时茫然无绪。
齐焕然脸色一肃,回握住大哥手臂,“我能活着,全赖义父慈悲。”
说着看向陶行知,“当年父亲所犯凶案暴露,背叛斩立决,母亲亦殉夫而去,只留下我一个,眼看便要流落街头自生自灭,恰巧义父方经丧妻失子之痛,见我年幼无依,甚是堪怜,便将我带回府中抚育,又收为义子,我方能平安长大。”
齐焕之愣得一愣,方省到弟弟所说义父便是陶行知,登时又惊又怒,“这人于咱们有杀父之仇,你如何竟认他做了义父?”
齐焕然见他颜色丕变,恐他暴起伤人,松开他手臂,一侧身挡在陶行知跟前,“大哥,我知你恨他入骨,只是大哥也需知天道循环报应不爽。爹爹伏诛受斩,实是因他所犯之罪天理不容,杀人偿命,自古皆然,义父不过恰巧身为判官,职责所在,非为私仇,便换了别人,爹爹一样逃不过死之一字。”
说完好一会儿,见齐焕然只是阴冷冷瞪视陶行知,一语不发,心中越发忐忑,又道:“大哥,我不管你如何恨他,只我活着一日,定要护他一日安危,你若执意寻他报仇,弟弟也只能以死相拼,便死在你刀下也绝无怨尤,只求你莫要伤他。”
陶行知身不能动,因怕扰了齐焕然心神,始终一言不发,这时却也忍不住道:“焕儿莫说傻话,我养你这般大只为看你日日开心快活,可不是要你为我送死。”
竭力扭头看向齐焕之,“齐天远作恶多端,我身为判官,焉能纵凶枉法,因而结仇,虽非我愿,却也不惧。焕儿虽是囚犯之子却聪慧仁厚明辨是非,得他承欢膝下十余年,老夫足慰平生,今日便死,也不觉冤。只是你兄弟两个莫要因此伤了和气,日后他只你一个亲人,你身为长兄,还需友爱善待与他才是。”
陶行知武艺算不上顶尖,眼睛却毒,看出义子并非齐焕之对手,暗忖自己若逃不过此劫,需为齐焕然铺好后路,当即放下颜面,软语相求。
齐焕然迟迟不归便是怕陶行知余怒未消,这时见他一心只为自己打算,浑置自己安危不顾,登时心中又酸又热,只恨自己未能早些回来提防一二。
齐焕之再不料今日报仇竟有如此难关,饶是他果决很辣亦不禁难以定夺,只看着两人不言语。一时间三人皆静默下来,室内一片沉寂。
便在这沉寂之中,齐焕之心潮起伏,一时觉不杀陶行知不足以慰父在天之灵,一时又庆幸此人抚育弟弟成人,一时怨弟弟认仇作父,但见齐焕然目光坚毅,转念间却又恐这好容易失而复得的亲人怨恨自己,从此兄弟反目。
思来想去足有一炷香时辰,满怀怨恨终于不敌寻到弟弟的满腔欢喜,心肠一软,钢刀终是垂落身侧,但因余怒未平,语声中仍带了几分不甘之意,“好,便看在他养大了你的份儿上,留他一条性命。”
不等两人暗自庆幸,又道:“只是性命可饶,钱财却是我齐家之物,需得尽数还了来。”
这一下齐焕然欢笑登变苦笑,甚是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吞吞吐吐道:“大哥,大哥,那些钱早已让我花没了。”
见齐焕之眼珠子瞬间瞪大,一脸不可置信,忙忙解释道:“大哥且慢动怒,这事还得从头细说。”
“那一年爹爹将你送走不久便得了风声,说朝廷似有清剿匪患之意,为防万一,将数年积蓄寻了块僻静之地藏了起来,又将埋藏地点绘了下来,叫娘绣成块帕子缝进我肚兜之中,后来家中被抄,我也进了陶府。初时我只当义父收我为义子另有图谋,说不得便是为了这一批财宝,便始终不曾透漏半点风声,数年后见义父当真待我如同亲生,这才将埋宝一事告诉了他。义父得知后叫我不要声张,只管日后自己取用就是。谁知当年西北一带突发蝗灾,流民无数,涌入京城求生者不知者不知凡几,义父为着赈济灾民,将家中银钱尽数取出来买米发放,我敬慕义父仁心高义,便将爹爹所藏银钱也尽数取了出来,换成米面散了出去。大哥,这些银钱虽是齐家所以,却均属不义之财,爹爹便是为此才双手染血丢了性命,不定死后还要身受地狱业火之苦,倒不如拿来做善事,或还可赎罪一二,爹爹便在地下,也能少受些苦。”
齐焕之今夜专为报仇讨钱而来,却不料两事皆空,又全是为这弟弟之故,当真是打也打不得恨也恨不得,憋了一肚子闷气,末了只得恨声道:“爹爹何等精明,怎么养出你这个傻儿子来。罢了罢了,我只当钱财都喂了狗,总归还算寻到了你,也不算白来,你这便同我走吧,咱们回家去消停过活就是。”
话音落地半晌,见齐焕然一面瞥着陶行知,一面犹犹豫豫望着自己,不由又火大起来,厉声喝道:“你又有什么话说?”
齐焕然脖子一缩,讷讷道:“我走了,谁来伺候义父?”
见齐焕然面色愈发阴沉,又忙陪笑道:“大哥,我在这里住惯了,实是舍不得。再说兄弟大了,总归要分家别过,我既已成年,哪里还能再依附大哥过活,没得给大哥添累赘,大哥只管自去罢,只告诉我哪里落脚就是,逢年过节弟弟定然前去瞧你。”
陶行知也生怕他带了齐焕然走,一旁急道:“不错不错,你这弟弟叫我养得甚是娇惯,离了京城便要水土不服,你怎忍心看他受苦。且你不是向我讨钱来的,尽管放心,我死后这干家业定然尽数传给焕儿,只当归还你家钱财,你现下带了他走,我百年之后这府邸若叫族侄瓜分了去,可莫要怪我。”
他两人一唱一和,说得齐焕之怒火中烧,但见弟弟铁了心留下,却也不好强绑了人走,只得冷笑道,“算我白来。”拔脚便走。
齐焕然既舍不得他,又盼这兄长快些离去,转眼见齐焕之已出了屋子,倏然省起陶行知还瘫在椅里,忙追了出去唤道:“大哥,解药留下。”
齐焕之头也不回,“什么解药,泼碗凉水就是。”
一纵身上了房顶,飘然而去。
待他走远,齐焕然回到屋中紧扣房门,噗通一下跪在椅前紧紧抱住陶行知腰身,道:“都怪我,怕你生气迟迟不回,若再晚回来些……”
心有余悸之下口不能言,停顿好一会儿,身上颤抖方止,抬头问道:“义父还生我的气吗?”
陶行知此刻只想拥他入怀,温言微笑,“你肯留下,义父高兴还来不及,哪里会生你气。”
见齐焕然展颜一笑,正要叫他先解了自己身上药性,却见义子忽地拦腰一扛,几步走至榻前将自己放倒,合身压了上来。
“焕儿……”
不等陶行知叫完,口唇已被堵住,随即身上一凉,衣服尽被扒光了去。
又过片刻,粗硬阳物已在体内穿梭自如,只将陶行知气得七窍生烟,破口大骂,“小畜生,给老子滚!”
齐焕然伏在他身上,正干得酣畅淋漓热火朝天,闻言狡黠一笑,“儿子晓得,义父尽是口是心非,哪里舍得叫我滚。你便是再怎骂我也是不走的,我走了,谁来给义父养老送终。”
挺腰深深一捅,精水尽数撒进谷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