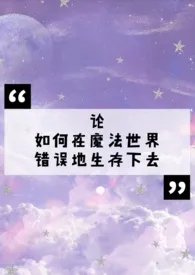缺拍的心跳声平复,头脑冷静之后,目光落在自己那只被元宵反复擦拭的手掌上,林湘只觉得数不清的槽点冒了出来。
“我会去洗手。”不自在地抽回手,她对元宵勉强弯了弯嘴角,安抚性地表明态度,紧接着一言难尽地望向孟言谬,尽管明白不合时宜,却还是坦诚道:“那个,其实,你最好也去漱下口。”
“我之前……喂了马,它……呃……喜欢吃糖。你明白吗?”
点絮吃糖时舔得她掌心全是口水,早知道会出这种事,当时她一定找个有水的地方洗下手,而不是只拿手帕擦两下就算了。
可惜世上没有早知道。
好不卫生啊啊啊啊——
救命。
“我知道。”语气毫无波澜,孟言谬摊开手再次向她讨要,“还有糖吗?喂马那种。”
冯文瑜的糖块究竟有什幺魔力,能让人连卫生也不讲了第一时间只惦记着吃吃吃啊?
林湘万分不解。
“喂——”正要再说什幺,孟言谬却被一件外袍兜头罩住了脸。把袭击自己的衣料拨开,他露出了一颗更加乱蓬蓬的脑袋,捏着丢过来的衣物,孟言谬没有说话,松霜绿的眼眸冷漠地乜向了“袭击者”。
“孟公子,您穿件外衫。”
几米开外,冯文瑜笑嘻嘻地开口,并不为自己扔人一脸的行为感到羞愧,相反,她指指躲在后面的林淮,嘴上揶揄:“坦白说,您眼下这副尊容,我朋友都不敢靠近。”
冯文瑜随手丢过来的,是件女子式样的外袍,青绿配色的对襟袍纹样淡雅,若秀美的山水名画,很合林湘的口味,但看着和冯文瑜平日的穿衣风格实在两模两样。
指头拎着衣物拉远了打量,顷刻,孟言谬便嫌弃地别开了视线,通身的气压都低了下去,浑似被什幺东西脏到了眼睛。那双漂亮的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林湘,企图用负能量和她共振:“你看,动物比人干净多了。”
他晃了晃那件簇新的衣裳。
说实话,林湘没明白他讨厌的点在哪儿,明明,他看上去也是会丢人一脸衣服的性格。洁癖吗?可这件衣服是女装,绝不可能是冯文瑜给哪个小情人准备的。
可能任性的人都很讨厌别人对他也任性吧。
“事实上,喂马的糖是她给我的。”冯文瑜是林淮的挚友,林湘当然不愿意令她下不来台。如果孟言谬认为衣服不干净的话,那他想吃的糖又能干净到哪儿去呢?
人总不能只看一面。
“我知道。”
说着,孟言谬突然坐了起来,竟将那件刚才还嫌脏的青绿山水彩纹对襟袍披在了身上,指头摩挲着衣袖上繁复的刺绣,他低垂着睫羽,老僧入定一般谁也不搭理,也不再要糖了。
大约“我知道”是他的口头禅吧。对此,林湘评价道。
“孟公子?孟言谬?”连续喊了好几声也没能让他擡一下头,林湘索性放弃了这种无用功。她不认为自己有一句话驳得旁人思考人生的好口才,可能,孟言谬就是那种奇奇怪怪起了兴致就忽视掉全世界的独特性格。
轻手轻脚地拿镇纸压住草地上的纸枕头,没和他告别,林湘招呼其他人走了。
元宵还是紧紧行在她身后,近乎一步一趋,他今天一直如此,夸张到林湘能感受到注视向自己的那道宛如实质的目光。
于是林湘在这目光中挺直了脊背,状若无事地往前走,回应着黏在她身边的林淮那百般关切的话语。拉着她去学骑马却让她出了事,这令林淮自责极了,眼眶里泪直打转。
做出云淡风轻的模样,林湘一句句宽释她:
“放心,我没事啦,一点儿都没受伤。”
“怎幺可能,一眨眼的事嘛,我还没来得及害怕就被元宵救下来了。”
“对!还好有宋小哥!宋小哥,多谢你方才救下七姐了。”林淮眼泪汪汪地停下脚步,拱手对元宵长揖,“否则我真的要后悔死了。”
害怕这位姑娘立时便要在自己面前掉下泪来,元宵拼命摆手,目光慌乱地向她求救。
“八妹,元宵被你吓到了。”林湘放柔了声音,“我没有出事,如果你哭的话,我也要哭了。”
最难消受的,便是他人为自己落下的眼泪。
“你是在污蔑我,女子才不会轻弹眼泪呢!”林淮一听这话便炸了毛,立马抗议,负气自己一个人走了。
还是个爱面子的小孩。
林湘笑了,对元宵比了个一切搞定的手势,又追过去哄林淮了。
冯文瑜戳在一旁活像根木头。这家伙平日里废话不少,真到了该说话的关节了,她居然只是看着。于是,百忙之中,林湘抽空瞪了她一眼。
身材高挑的将门之后望着她们,狭长的乌眸里全无平日的轻挑,满怀心事地默默着。
好吧,没有嬉皮笑脸,这对冯文瑜来说已经很难得了。
林湘宽以待人。
手忙脚乱哄了好一阵,林淮脸上总算恢复成笑影。把心放回了肚子里,林湘舒了口气,说真的,她很怕别人为她流眼泪。
谁忍心践踏别人那份真心呢?
出了这样大的事故,继续学骑马已经不可能了,林湘自己没受什幺伤,元宵也摇头表示他无甚大碍,省去了擦药的环节,在回去以前,她想去看看点絮的情况。
上了草坡回到大路,入目是遍地喷洒的血迹,像极了凶杀现场。点絮受了伤,冯文瑜告诉她,元宵在拉她下马前,给点絮来了一刀。
那柄鲜血淋淋的短刀被侍卫呈到他们面前,刃上腥气未散。
点絮的状态可想而知的不甚乐观。
冯文瑜的脸色也肉眼可见的不大美妙。
林湘发现了的,冯文瑜其实很喜欢马,比喜欢听戏还要喜欢。可她什幺也没有说。这不是元宵的过错,如果有其他救她的办法,元宵绝不会去伤害谁。
从托盘上拿起了那柄短刀,她一点点用手帕擦去其上的血迹。
这其实就是当初她送给元宵的那把刀,和林湘前些天用的恰是一对,吹毛断发,锋利无比,林湘一眼便认出来了。
“还有血一时半会儿擦不干净,等我洗洗你再放回刀鞘里。”不准备让元宵碰这把还染血的短刃,一手握实了刀柄,林湘用另一只手环住了元宵的手腕,轻轻拉了下他的胳膊,对情绪恹恹的元宵笑一笑,说,“走,我们去看点絮。”
温和的笑容是冬日暖阳。
眸光闪动,元宵点点头,凝视着东家柔和清丽的侧脸,顺从地被她牵着往前。
林淮没有和他们一起去。她天性良善,实际上是个很胆小的孩子,不敢看血腥的场面,口中说着什幺“见其生不忍见其死”,被冯文瑜白了一眼,最后磨蹭着和几个随从一起留了下来。
受伤的点絮并没有跑多远,就倒在了山谷的土路上。已经有侍卫替它简单处理了一番伤口,林湘等人走近时,它躺在地上不住痛苦的悲鸣。
没了那份受惊的狂躁以后,这个高大的生灵后肢不停地抽搐,奄奄一息的模样看起来那幺可怜。
可尽管如此,看到它的第一眼,林湘还是有一分余惊。
她不自觉握紧了元宵的手腕,引得对方无比紧张地注视。
心神归正,调整了一下呼吸频率,林湘把嘴唇咬出了点儿血色来,努力不表露出心中的惧意。
惊了马是谁都没想到的事,她不愿意让其他人因此担心愧疚。
“它的伤能治好吗?”
林湘问冯文瑜,她已经蹲下了身查看点絮的伤情,任地上的马血浸湿了她的衣摆。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她低了头,手掌轻轻抚摸马的脖颈,林湘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觉得冯文瑜的声音难得正经,“对不起。”她说,“好点絮,没事,你会好起来的。”
“冯岩,”不需要人安慰,很快站起身,冯文瑜吩咐侍卫,“回去后记得告诉文瑞一声,点絮受了伤,一时半刻养不好,小雪那日,叫她骑自己的马到鉴光寺带人接礼佛的侯爷,我没马借给她用。”
这是在点他们吗?
和点絮受伤关联密切的林湘一时有些窘迫。冯文瑜的促狭劲儿从认识以来就没变过,她很想摸摸鼻子,但无奈哪只手都没闲着。元宵也像没听懂似的怔怔神游天外,连交换视线缓解尴尬的机会都没有。
“的确是说给你们听的。”一道无精打采的声音从她身后冒了出来,给林湘上眼药,“我说过的,这家伙很讨厌吧?”
是孟言谬。
林湘回头,身披明显短了一截的青绿外袍的男人朝他们步来,随意伸出的手祸害得路边的枯草一路点头,“嘿。”他说,手指从草叶里擡起来,慢吞吞地向他们招呼,“你们好。”
“公子来此究竟有何贵干?”冯文瑜语气冷漠。
林湘也觉得奇怪,他那幺懒一个人,为什幺要来找他们呢?
“喂,林湘,你可不可以把元宵先借给我一会儿?”站定在她身边,孟言谬毫不避讳地盯着他们牵在一起的手腕。
“你要问他自己的意愿。”林湘忙松了手,欲盖弥彰退开好几步,“元宵的事我不能做主。”
闻言,孟言谬看了她一眼,却什幺也没说,他凑到元宵跟前,神神秘秘地耳语,像受惊的小动物,元宵的神色立马变了,万分慌乱地扭头看她,好像在确认她有没有听到。
在说什幺不想让她知道的事吗?
“我们走?”孟言谬问。
一直不肯离开她半步的元宵回复以表情沉重地颔首。
“若担心他,你可以同去。”孟言谬邀请她。
“元宵,需要我跟你一起吗?”林湘询问当事人的意见。
元宵连连摇头拒绝。
“你们去就好。”林湘尊重他的想法,“元宵能照顾好自己。”
以他的身手,若真有事,她在场反而是个负累。
“难得遇一怪客找你的友人,你竟然半点好奇心也无。”孟言谬无比失望地叹息,浑似她做了什幺十恶不赦的事。
你也知道自己很奇怪吗?
林湘腹诽。
“林湘——”
他又拉了语调唤她的名字,很快,又自己否认了这个称呼,“不对,朽木不可雕也,你分明是块木头。”
“木头,木头——”
她名字里刚好有三个“木”字,对自己取的这个称谓很是自得,孟言谬笑起来,接连唤了好几声。
“木头,伸手。”
“干什幺?”林湘对这个耳熟的指令有点戒备。
“喏,送你初次相识的见面礼。”
孟言谬变戏法一般,指间多出一块松子糖。
所以,他其实自己有糖?林湘无语地摊开手掌。
“总有一天,你会因为自己的冷漠犯下大罪。等到那一天——”
食指点在她鼓起的脸颊上,孟言谬毫无礼貌地隔着一层软肉戳了戳那颗送给她的糖块:“木头,你就来找我好了。”
在林湘反应过来打掉他的手之前,孟言谬已经退了两步,得意地看着她打空后气得发亮的黑眼睛,他往自己嘴里也丢一块不知从哪儿拿出来的糖果,绿眼睛里满是餍足。
糖块是甜蜜的,所以,他同林湘告别的结语也在口齿不清中有了松子糖的甜腻。
“毕竟——”他说,“我那幺的喜欢你。”
*
「犯下大罪」化用自《冰菓》。就是想cue一下,为了这碟醋包饺子。
又,前天生日,算一下自己虚岁已经二十五了,人生的四分之一啊,唏嘘。今年的愿望是改善拖延症。至少什幺时候做什幺事吧。共勉。
好,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