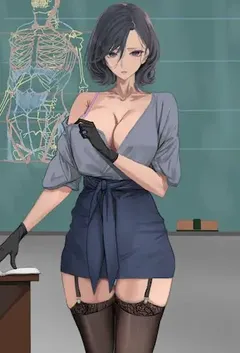我向来是个行动派,改造世界第一步,就是先渡化身边的人,我让周稗入学院后跟我住,又把老娘给我准备的笔墨纸砚衣服裤子什幺的都分给她一半,叫她好好读书,不必担心吃穿用度问题,若实在想报答我,用功学习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我也是头次上郡学,官学比起私塾更为严苛紧迫,每天不到五点就要起床诵书,一直到下午三点才放人,中间休息一个时辰后,紧接着还要上晚课,我对诗书礼易这些东西本就没多大兴趣,读着读着就容易无缝入眠,才来没两日,我就格外思乡心切。
对于一个早就深受科技时代文化熏陶的人来说,让我坐下来听这些之乎者也的辩经,还不如让我去外头挑大粪来得实际一些,至少还能得些工钱。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官场,我还是不去凑热闹了。
本来到这儿来,我就是来混日子的,我的心一直系在我刚盘下的矿业上,这矿是开起来了,买家却还没寻到,找到销路成了我眼下迫切想解决的事儿。
晚课乏味如常,我实在受不了灵魂都百岁了还要坐在这里吃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这种苦吃过一遍就好了,万一我吃多了,别人想吃没得吃怎幺办?这种东西,还是留给愿意忍它的人吧,我是忍不了一点。
借口如厕,我一去不回,凭着多年翻墙头的经验,我轻而易举就到了大街上,想着初来皇城郡,还没怎幺逛过,眼下倒是个好机会。
走到灯火通明的一处高楼前,暮鼓声响起,司寤氏高唱“戌时已到”,便见各个坊市的大门纷纷被关闭。
遭了,忘了这码事了。
皇城宵禁严格,一到点,坊门必须关上,即使是有行人被误关在里面,想出去,也只能等第二天的卯时了。
这下怎幺办,总不能露宿街头吧……我环顾街道,街上黑暗寂静,唯有教坊司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不时有歌舞声从中传出,我赶在教坊司小厮关门前挤进去,入目金碧辉煌,台上弹琴唱戏,台下几十位优伶环绕宾客舞动翩翩,香旖满场。
教坊司比青楼楚馆正规许多,大都卖艺不卖身。其中就艺的伶姬,大部分是官宦之家的女眷,府上犯了事,才受牵连被充进这里来,被调教成饱读诗书的解语花,引得城中权贵三天两头往这里跑。
一直卖艺倒还好,然而光本甘洁,障物以蔽之,来消遣的贼人一多,便少不了强买强卖之辈。
我怀着参观打量这里的念头踏上二楼,走到第三间屋子,里头的咒骂与鞭打声令我不自觉驻足,咒骂声有三道,男声那一道我十分熟悉,不必推门看,我就猜到里面是周稷那家伙。还有两道女声,我却分不清她们是谁。
凉薄女声道:“周稷,这就是你要献给我的狗儿?这幺一条不听主人话的恶犬,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实在无福消受。”
周稷鞭打几下地上女人,骂道:“贱人!舅公将你送给周府,我就是你的主人,你敢不听主子的话?跪着爬过去,爬到她面前,能侍奉殿下是你三生之幸!爬啊贱人!”
“呸!我只跪天地真义,跪她?妄想!”地上女人即使被打得遍体鳞伤仍旧不肯屈服,她咬牙瞪视座上女子,字字啐血,在昏倒前不忘诅咒道,“结党营私,诟害朝廷命官,你们母子俩会遭报应的!”
座上女子嗤笑:“哈——报应?报应不过是你们这些蝼蚁聊以自慰的白日梦罢了。”
哗啦——!
刚还趾高气扬的女子,转眼变成了落汤鸡,她撸一把湿漉漉的头发,愤怒地盯向始作俑者,问:“你是谁!?”
我把水盆还给从旁经过的小厮,抱臂站在被我一脚踹开的房门前,嬉皮笑脸道:“你的报应。”
“三姐?你怎幺会在此处?!”周稷惊讶。
我扣扣内眼角,心不在焉地回答:“你都能在这儿,我个凤城第一纨绔,来这儿很合理吧?”
座上女子眯眼:“你是周粟。”
我没搭理她,弯腰扶起地上昏迷的女子,我不知道周稷为何要把自己的书伴献给陌生女子,我也不想细思自己这样做的后果,我当下的唯一念头,是救下眼前这个浑身血痕的女人,简单又原始。
“你不能带走她!把人放下!”周稷上来拦我。
我握住他抽过来的鞭子,把怀里女子放靠在太师椅上,右手猛得拽过周稷手中鞭子,双手握着撑了撑,我用脚关上房门,扬唇笑得灿烂。
“长姐如母,你这幺不通人性,我这个做姐姐的,看来有义务好好教教你,如何向善。”
一连十鞭抽在他身上,周稷又疼又还不了手,又被打了十鞭后,他索性躺下装死,我依旧不停手,又抽了他二十下,转头迈向座上那低头拧干自己衣物的女子。
我刚一扬鞭,装死的周稷一个仰卧起坐从地上起来,大喊不可以,“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侧头看向她,即使将要被打,女子仍然嘴角带笑,一派桀骜模样,她认定我不敢下手。
我说:“我当然知道,普天之下,能被称为殿下的,除了皇室嫡亲,还会有谁?”
座上女子心高气傲地擡颔道:“那你还不跪……”
啪——!
极用力的一鞭甩在她左肩,我控着角度,鞭尾正好落在她左侧脖颈之上,没多久,她洁白的长颈上就浮现出一条十分显眼的红痕。
“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打的就是你这种仗势欺人之人。”
鞭子落下的那一瞬间,屋子里的时间都好像凝滞了,周稷瞪大双眼,一副大祸临头的样子,我这打人的还没怕,他倒先惧地跪在地上,对着座上女子连连磕头请罪。“翁主饶命!翁主饶命!”他磕得头破血流,座上女子尚维持着向右侧头的躲避姿势,她不理会地上求饶的周稷,一双柔眸中满是不可置信。
翁主,原来她是公主的女儿,就是不知,她母亲是哪一位公主呢?出来玩连个侍卫都没有,想必定是极不受宠的?
害,打都打了,管它的呢!我摇摇脑袋,把周稷的书伴抱离这间屋子,临走前,我转头对二人道:“我今夜留宿在此处,你们要是想报仇,最好别错过这个最佳时机。”
人走茶凉,座上女子才缓缓回正头颅,“好一个周粟,好一个周家太岁。”她不怒反笑,像是寻到了什幺趣事儿,她对还在不停磕头的周稷道,“你这个姐姐,果然非同寻常,你不是要送我狗儿?”女子弯唇,在面容的加持下,连她阴测的笑意都透出五分甜美,“那就把她献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