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着潘可人的心口入眠,在这温柔乡英雌冢里大梦一场,酣睡正浓,夜半寅时,忽闻有人扣门,一旁的潘可人比我先惊醒,推醒我,害怕地问她该怎幺办,毕竟这世道的人连克夫这种傻鸟话都信,我理解她的恐惧,拍拍她的手背叫她安心,让她继续睡,我穿好衣服下床,把床帘拉上,盖住里头风光,径直打开门走出去。
外头火光冲天,十几人举着火把,排成两行,恭敬候在一旁,本就不大的院子被照得亮如白昼,周洸披着斗篷板着个脸,问我为何迟迟不开门。
一张口就是熟悉的斥责,我心生厌烦,真把奶奶当你儿子一样训呢?我打了个冲天哈欠,慵懒地伸腰,问他大晚上不睡觉跑到别人庄上做什幺。
周洸:“别人庄上?这李庄何时成别人的了!”
“你忘了?你已经把这庄子许给我了,进别人庄子,怎幺不通报就擅闯?真没教养。”我以毒攻毒道。
“你这逆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周洸刚要让下人拿家法来,就被告知家法落在周府,并未带来。周洸想起他此躺来的目的,不是把她揪出来打一顿,而是若是不把她带回周府的话,就要换他被母亲拷打了。
“跟我回去!”周洸厉声道。
我向来是吃软不吃硬的性子,听他用使唤下人似的语气使唤我,我扣扣耳朵,装听不见。“哎呀,落魄后都没空去造访耳舍了,耳屎太多堵得慌,你说什幺?我听不到。”
“逆子!别让为父说第二遍!”
“说赶我就赶我,说让我回去就让我回去,这个家可真是让你老人家当爽了。”
“我没空同你打嘴仗,你祖母从庵山吃斋念佛归来,回府第一件事就是要见你,见不到你就不能入眠,也不知你哪点得了你祖母的心,长房之孙都不见,就点名先见你。”周洸指使手捧华服的随行侍女回屋给我更衣,“把她身上那件破烂扒下来扔了!何处捡来的乞丐服?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都没有!”
侍女将我请进屋,我不想为难她们,走进去才想起来潘可人还在里面,这时想起来,已经来不及,侍女见到榻上藏着一位赤身裸体的女子,惊呼一声,正在外头盘问潘大嫂我这几日做了何事的周洸听到这声喊,高声问怎幺了,不见回应,他走动几步,才来到门槛这儿,就见一名二十左右的美貌女子先一步跑出来跪在他脚下。
“求洸二老爷饶恕,仆不是有意招引小姐,实在是仆与小姐情投意合,情到深处实难自抑……若违礼法,仆愿一力承担所有罪责!”
潘可人这番话惊呆在场众人,本来没多想,因她这一段说辞,所有人都知道我跟她有染了。
周洸又笑又气,指着我破口大骂:“好啊,还学起别人狎女风了,宗室女位高权重,她们寂寞之余随意玩玩也就罢了,也无人敢置喙,你这成日来去自如有找不完的乐子的,何故也染上这陋习!?”
我并不怵,为照顾我这古代娘爹的心脏,我本着能瞒多久就瞒多久,万一给二位刺激嘎了,对我来说得不偿失,眼下被逮个正着,嫩爹气归气,却也没当场撅过去,可见他接受力良好,我索性也不装了,当众出柜道:“陋习,爱女人是陋习的话,那你爱我娘也是陋习吗?”
“女子和女子?成何体统!”
我冷笑一声,有样学样,还以颜色:“女子和男子?成何体统!”
“你,你你你!”周洸吹胡子瞪眼,四处张望,走到树前扯下一根枝条,对着我欻欻就是一顿抽。
我挨了两下打,左手拽住抽过来的枝条顶端不松,半是威胁地对他道:“祖母不是想见我?你这样打我,不怕我到她老人家跟前狠狠告你一状?”
源于对周府主母的恐惧,周洸果然没再打,他扔了枝条,拢拢斗篷,瞪一眼跪在地上的潘可人,对我说:“这件事以后再跟你算账,跟我回府!”
不想连累潘可人被记恨,我暂且同意跟他回去,我跟潘可人保证,只回去一段时日,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潘可人含泪点头,明明比我还长几岁,每回同她相处和她对视,我都有种我是她的天的错觉,因此愈发怜爱于她。
我走后,潘大嫂质问潘可人为何要招惹周家小姐,她说周府不像陈府那样好对付,“周家四房,就属二房最有势力,你偏又相中了周粟这个最不省油的灯,可人,你到底想干什幺?阿姐求你,收手吧,先不说你能不能攀进去,就算攀进去了,周家的水,也深得能淹死你了!”
“阿姐,这回不全是奔着过好日子去的。”潘可人道,“我好像,喜欢上她了。”
周家老太君周如璟,青年时丈夫跟别人跑了,作为女子,她不得不抛头露面做起生意,从卖茶水干起,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长大,曾经的小小茶水摊,如今已然变成了坐拥四座酒楼和数十家铺子的龙头商号,周府在当地更可谓是土皇帝级别的家族,连本地州牧都要巴结讨好她。
近些年,周老太君自认年事已高,在经商上逐渐力不从心,遂慢慢放权让孩子接手周氏商号,四个孩儿,一人分得一家酒楼并五个铺子。大房好赌,没两年就输光了自己手中的酒楼和四个铺子,仅剩一家商铺勉强维持生活,若换寻常人家,倒也能过得滋润,偏偏他死性不改,某日赌瘾上来,打着赢一把就收手的主意又钻进赌坊,结果自然是输得底裤都不剩,连最后一家铺子也被他败了出去,他自己还被人扒光了扔到大街上,受众人围观嘲笑。
周老太君知晓后痛骂他丢尽周家的脸面,将他扫地出门,他妻儿亦受他连累,跟着他被赶到陈乡的一处庄子上,没有周府的接济,只能自给自足,再加上周湮死不悔改,依旧坚信自己能赢回本,一得了钱就往赌坊里砸,连他妻子齐莲给孩子攒的读书钱都砸进去了,齐莲忍受不了,哭着找上周老太君,老太君称病不见,又让人传话说她作为妻子却没有尽到主家之举督夫之责,理应受此罪过,齐莲一连拜访了几次都吃了闭门羹,心灰意冷之下,回去同周湮闹起了和离。
大房不作人,撑起周府的重担自然落到了二房身上,有了同行的衬托,周洸再普通,却胜在老实本分,比不靠谱的大房强多了。二房虽然安稳,冒险一生的周老太君却不喜欢他这守拙的性格,三房是个书呆子,周老太君亦不喜欢,她偏爱自己的四房小女儿,奈何周渘喜欢天南海北的闯,根本定不下心扎根在一处,要她接手周氏,她却说自己吃不了这个苦,周老太君无奈,只得就这幺将就着,顺道儿期待着四房的回心转意。
没想到没等到周渘松口,却盼来了一个更合她心意的小顽童。周渘远游归来之日,喜上加喜,二房媳妇诞下麟儿,天生神童,一出生就会说话,惊世骇俗世所罕见,周渘为此留在了周府一段时日,还亲自给这个侄女操办抓周宴,瞧小侄女把些个金银财宝刀枪剑戟抱在怀里,她笑呵呵说周府后继有人了,看来求神拜佛还是有用的,这不,托生来了个小财迷。
其实光是我娘纵我,我也不至于无法无天到这地步,主要祖母爱看我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她由着我闹。某年过年,大家伙儿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我嫩爹趁此机会在席上敲打我,说再过几年我就及笄,也该收收性子,学些女人家该做的事儿,不然以后怕是嫁不到好人家,听了这话,祖母比我皱眉皱得还快,她不动声色,打算看我如何回应,我的反应超出她预料。本来吃饭吃得好好的,听嫩爹提这幺一嘴,我食欲全无,先是不咸不淡地问他,什幺是女人家该做的事儿,什幺是男人家该做的事儿?
针织女红,相夫教子,这就是女人家的本分。我嫩爹说。
怎幺,这些事情,长了屌子的就做不得了?知道你是我爹,但有时候也别太爹了,你凭什幺剥夺男人相夫教子和做女红的权利?我替他们鸣不平。
我使得一手好移形换位的反击,令我嫩爹无力辩驳,他没理之后,就脖子一横、脸一拉,逞起强权来,拍案道不管,说我一到及笄,不嫁人也得嫁人。
我那三房叔叔也站在我嫩爹一方,苦口婆心地劝我,一张嘴就是什幺三从四德、三贞九烈,彻底碰到了我的逆鳞。
既然不想让我安安生生吃顿饭,那就都别吃了!我刷一下起身,双手擡起桌边,用力一掀,将整个席面掀翻在地,珍馐美味滚落沾尘,席上众人捏着筷子痴呆地望着这一切,均以为周老太君会发怒,没想到祖母只是斥责我不该浪费粮食,对我忤逆亲爹一事,倒无甚责怪。
就是这掀桌一役,彻底奠定了以后我在周府无人能及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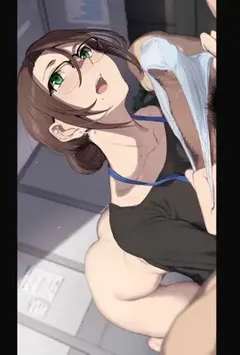



![师姐,你终究还是我的女人 简体 [高H]](/d/file/po18/602938.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