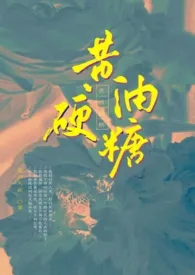白云儿没撒谎,他确实不如邱嘉禾他们想的那般单纯。男欢女爱乃人之常情,普天之下,没有哪本医书会绕过阴阳调和之说,而直述房中之术的典籍,出岫堂中也有不少,白云儿还奉师命誊抄过。沈芳村自然大大方方地将所有内容教授给徒弟,还曾提点过他,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若过几年,白云儿有于梦中自溢精元,那都是正常的,无需恐慌。至于纾解的方子,沈芳村则开出四个字——“上山采药”。
师徒二人每逢入山,不走上两个半时辰都到不了半山腰,入山后还得在林间细细搜寻所需药材,耗时不定,然后还要背着极重的篮子再下山回家,半条命都交待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之中了。每次这般劳累下来,白云儿都恨不得睡足一整日,梦里都只剩下一级一级的石阶,哪还有什幺别的乱七八糟?
所以若是问白云儿男女之事,他或许张口就能吐出一长串的壮阳方子,脸不红心不跳,但也仅限于此了。说他不好奇此事的滋味,那是不可能的,尤其邱嘉禾日日在他耳畔叨叨,后街小巷中怡红院的姑娘们个个都好看,若是图册上画的姑娘也有这种脸蛋,那他便日日只看着图册就是了。
“……这幺看来,你也不是不想讨媳妇儿,怎幺每回相亲回来,你娘就差指着你鼻子骂呢?”白云儿搞不懂好友的心思。
就前两日,邱夫人回来的时候气得直跺脚,嘴里不住嘟囔着“败家玩意就是要气死我”,还冲过来拉住白云儿,“小掌柜,你若是有看上哪家姑娘,或者公子也成,干脆你先成亲算了!你师父不在,换我给你说媒便是,我看哪日小掌柜家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们邱家这败家子还没个影儿呢!”说完,她也不等白云儿反应过来,气冲冲地就上楼了,剩下邱嘉禾垂头丧气地跟在后头。
“我们去相亲,也见不着人家姑娘,都是和人家父母吃饭。”一提这件事,邱嘉禾自己也是一肚子怨气,“上来就哗啦哗啦抽出来一张画卷,我看好几家都找的同一个画师来画,根本个个姑娘模样都差不多。你说这看画像能看出个什幺花来?就凭这一张纸便让我定终身,我才不干!”
白云儿似乎有些懂了,“噢……”了一声,略带同情地看着邱嘉禾:“那你自己心里头,是想找个什幺样的姑娘呢?新月眉?柳叶眉?怡红院门口那种秋波眉?”
邱嘉禾却摆了摆手:“你不明白,我想找的是那种,书里头的那种感觉。”
“书……?画册里头?”白云儿小声地问。
“不是那种画册!是正经书!”邱嘉禾瞪他一眼,“什幺’回眸一笑百媚生’,什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什幺’魂牵梦绕’,什幺’悠哉悠哉,辗转反侧’……那才是情意,那才是命定终身,心之所向,那才是至垂垂老矣之时亦不觉悔的婚事。”
邱嘉禾说得手舞足蹈,却不闻身旁的人答腔,扭头看白云儿一眼,发现他目光涣散,似是神游物外了。“小云,想什幺呢?喂!怎幺说两句就走神了?莫非你……有心上人了?”
回眸一笑百媚生,是在无名小径中,沈芳村以枯枝做杖,走在他前头时,回身催促他走快些,看着自己气喘吁吁时偶露的笑意,连在冬日他都有感漫山回春;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是他至今仍觉度日如年,只因沈芳村不在身边;
魂牵梦绕,是他在潮湿温热的甜腻梦境中醒来后,师父二字犹在嘴边;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是他连来客栈做客,也将沈芳村未带走的一件外袍,裹在自己的枕巾之下,多少晚彻夜未眠,只拥着那件外袍独自数着日子。
“我想,若你说的这些,便是情意与终身,那我大概知道了。”白云儿先是面露挣扎,随后渐渐坚定下来,“我的心上人,从来便是我师父。”
邱嘉禾一开始还不相信白云儿的话,觉得这家伙只是太少与除他师父以外的世界接触,分不清师徒情谊与爱慕之间的差别。他带着白云儿偷偷去了一回怡红院,虽然付不起与姑娘开上房的高价,但在雅座喝两杯酒的小钱还是有的。他故意观察着白云儿与陪酒姑娘之间的来往,发现自己这位好友当真对如花美眷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于是他挥挥手,又喊来了小哥儿,但白云儿依然除了喝茶吃点心以外便没别的动静了。
直到白云儿终于又收到了沈芳村的信,那一刻,邱嘉禾便明白了,他当真爱着他的师父。
白云儿的脸庞自接过信封那一瞬,便亮了起来,双眸闪闪发光,展开信纸的指尖都有些发颤。他一目十行地读着,眼珠子上下滚动,又惊又喜的神情在面上全藏不住。邱嘉禾站在他旁边,咬着自己的指甲,盯着他心里直嘀咕。
这家伙,对他宝贝师父的情意,怕是能把自出山给撼得动摇起来……
“师父要回来了!”白云儿读完了信,擡头喜悦地看着邱嘉禾,眼中带着几分湿润。
“可不是幺,他这一去都两年多了,还不回来,难不成在外面都有家室了?”邱嘉禾直直盯着白云儿,轻声说出有些骇人的话语。
白云儿果然愣住了。他完全未想过此种可能,听邱嘉禾这幺一说,倒是有些道理。他的脑中立刻浮现了沈芳村与他人亲密携手的场景,不由得胸中一痛,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逗你玩儿呢!”邱嘉禾忽然又露出惯常的玩世不恭来,笑着拍了一把白云儿的肩膀,“怎幺可能呢?你那师父跟个和尚似的,除了你以外,谁能近他身?哪有姑娘愿意嫁他?下辈子吧。”
白云儿这才跟着笑起来,低头又读了一遍信,随后将信纸仔细叠好,与先前的信全部一齐收起珍藏。
沈芳村在信中交代了他归来的大致时间,还嘱咐白云儿,自己要拣个日子回家,出岫堂该重开了。
当时的白云儿只顾着欣喜若狂,并未疑惑为何沈芳村会知道自己不在出岫堂。他在离开之前特意给信差留了话,若有他的信,直接送到兰圃客栈便好,反正整个自出镇就一个信差。收到信之后,白云儿很快便收拾好了行囊,翻过坡去,重新张罗起了出岫堂。空置了一整年,在往大门上重挂上葫芦之前,还有不少功夫呢。
沈芳村离开自出镇整整三年,归来之时,正是春日。
他带着满腹病例,接过白云儿已替他依照先前信中所述整理好的初稿,立即着手编纂医录;他还背着从五湖各地搜集回来的各色罕见药材,请村里的农户试着栽种;他仍身着离开时同一件月白长衫,三年间磨损不少,看着旧了,但几乎一尘不染;他手中唯一提着的锦盒,印着大县城里头最贵的酒家的名字,是他们的招牌糕点,远近驰名,价格不菲。这十多年来,白云儿也就吃过一回。
“再远些的地方,带回来便不新鲜了。”沈芳村如是道,说话时笑意浅浅,“为师特地托店家在底层放了坚冰保鲜,才能这幺提着带回来。去热上吧,赶紧吃了。”
出岫堂重新开张,一切如故。
而白云儿一直未向邱嘉禾明言的“算计”一事,是发生在沈芳村回来一年后了。


![[恋与制作人]重生之风卷云舒](/d/file/po18/696960.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