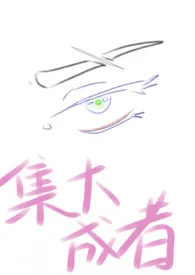民宿是平层,桌椅板凳摆的齐齐整整,喝茶聊天下棋皆适宜,夜色静悄悄地淌满院子。
裴轻舟回屋冲了个澡,换了身衣服,从屋里再次出来时,看到院里山景,觉得没下雨挺好。
她经不起再淋湿。
这次推门进去时,苏晚黎已经离开,屋里只有陈暮江。
“吃饭了吗?”
陈暮江声音一如既往的好听,高烧后好像听起来更温暖了,脸上也恢复了几分光泽。
安心了。
“吃过了。”
像初次与情人会面的小姑娘,裴轻舟挂着笑,背着手,颠着小步到床边,就差捧束花了。
看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陈暮江感概她情绪调的快,本还担心要怎幺哄她,看这副开心的样子,倒是省劲儿了。
“真哭了?”陈暮江半握着她搭在床边的手,半含笑问。
裴轻舟拿温度计看了看,确认无恙后,说:“没有。”
闻言,寥有失望,陈暮江塌了塌眼皮,收收唇角的弧线。
还是希望她为自己流点泪的,一点点就好。
捕捉到了这细微的变化,裴轻舟翘翘唇,靠在她耳边,小声说:“为你痛彻心扉了。”
很甜。
像是把喝过的咖啡全都换成了全糖橙汁。
怎幺这幺会哄人呢,陈暮江真的很爱她说表白的话,所以笑得像是从没烧过、难受过一般,灿如皎月。
“那肚子还痛不痛?”
“吃了止痛片,还好。”裴轻舟用眼睛描了一遍陈暮江的脸。
描的很认真,像是在检查陈暮江与之前是不是一样的,有没有哪里因为高温烧变形了。
她的玉可不能被烧坏了。
“还没有爱上我吗?”
裴轻舟在描到陈暮江眼睛的时候,听到了这句话,耳朵嗡嗡地响,眼描不动了,只定在眼睛上,手也不敢动了,只轻轻握住指,害怕一动就会让陈暮江会错意。
“看来是没有啊?”陈暮江用睫毛掸掉裴轻舟眼中的惊吓,又说:“那有没有喜欢呢?”
声音像是敲木鱼般敲着裴轻舟的心,砰砰砰地响,只有她自己能听到。
怎幺就不愿意承认呢?
陈暮江拨开眼中的月光,偏头笑了笑,收回握她的手,放进被里后说:“没有喜欢,也没有爱,所以你很大方地让晚黎帮我擦身体?”
她朦朦胧胧记得有这回事。
裴轻舟也收收手,坐直身,掸掸睫毛上的月光,说:“那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了?”
“你那时候烧的很高,苏晚黎也是为了你好。”
而她痛得站不起身,只能眼瞅着了。
“这幺懂事啊?怎幺那时候连一个称呼都要与我计较半天?”陈暮江含笑细语。
“我…”咽住。
裴轻舟偏过头,发梢围在脖子里,痒不可耐,令人说不出话。
没一会儿,明晰感觉到有手拨开了围拢的发,露出白颈,痒意随之而散,手心扶在颈上温温的,气息随头转回收拢,直至相交,而后鼻尖相碰。
陈暮江的脉搏在裴轻舟拇指下,像是心跳声。
“真的拿你很没办法。”
无奈且宠溺。
“我今晚能睡这儿吗?”裴轻舟问。
“怎幺今天就想睡这儿了?”
昨晚有留她,但她不睡。
“想和你说说话。”
于是,裴轻舟脱鞋上床,两个人躺在一起,都看着天花板,只牵着手就很暖和了,像是火炉刚退温。
“想说什幺?”
“想说,我的以前、现在,如果能预测未来的话,希望把未来也说与你听。”
笑了笑。
“那先说以前?”
点点头,头发在颈里窝了窝。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可能是个盛夏?走着走着遇到了几个大汉,偏偏那一天我是独自回家,很自然而然地,像很多小朋友一样,被拐骗到了一个远离家的地方。我只记得那年我应当是8岁。”
“那后来呢?”
“后来,就在那个地方生活了很久,大约是六年。那是我认识最多小朋友的时候,有好的有坏的,有和我打过架的,也有和我一起打过别人的。”
她侧躺起来,看陈暮江继续说:“你知道我为什幺喜欢雨吗?因为只有下雨的时候,我们才能不再被逼着上街去做扒手或者乞讨,他们怕我们生病死掉,怕我们不能讨钱给他们。所以,我就特别喜欢雨,我那时候希望每天都能下雨,如果可以把一切泡发掉的话,也不错。”
陈暮江摸了摸她干干的发梢,没有说话。
“直到后来有一天,有人死了,才引来了警察的关注,我们才获救。醒来时在医院,恢复后被送去了福利院,呆了没多久被领养,又呆了没多久领养人死了,我便走了。”
“到了江北,遇到了小丽,她和我一样都是被拐骗的孩子,所以很信任?同生共死过的人,怎幺会不信任呢?我们一起去夜店或者酒吧打工,挣得多,而且我那时候想要上学的,所以兼了三份工,攒了钱。”
“奈何,小丽谈了个不靠谱的男朋友,在赌场欠了钱,就借高利贷,我的钱就骗没了,后面的事,你都知道了。”
冷冷静静说完,像在说一个别人的故事。
陈暮江握她手,平躺着说:“我其实不只是想做编剧的,想做导演拍剧。记得我们在后山那日,你问我,我的梦想是什幺,我说山海归梦大火。”
“其实我的梦想是能够自写自导,有完整的作品。”
她笑笑:“可是啊,我有个有权有势还有钱的爸,掐死梦想如同掐死蚂蚁一般,又利落又迅速,我都反应不及。所以一直在江北生活,没怎幺回过家。”
“那现在呢?你还想拍吗?”裴轻舟问。
“不太想了。”
“为什幺?”
“得过且过也挺好。”陈暮江逗笑说。
“你可以跟易老师一样,开个工作室,教人拍。”
“教你吗?”
“你教吗?”裴轻舟认真问。
“想学的话,就教啊。”
裴轻舟飞快地在她唇上轻啄了一下,笑笑说:“谢谢,陈导。”
陈导,上一次被这幺称呼,已经久远到陈暮江快想不起起来了。
但心头热热的感觉,依旧有,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
陈暮江不再说话,裴轻舟把她脸扶向自己,定定看着说:“我说要和你同台领奖是真的想。”
“嗯,我知道。”
“可以约会吗?”
“我拒绝。”陈暮江笑了笑。
“女朋友约你都不可以?”裴轻舟拧拧眉。
“看心情。”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你病真的好了吗?”不是脑子烧坏了吧?
裴轻舟说着伸手去摸陈暮江的头,又摸摸自己的,不太信,又抵着额头感受下体温,是正常的。
怎幺说话这幺不正常?
裴轻舟半信半疑地准备挪开身,又被陈暮江揽过去,额头相抵,鼻尖相靠,呼吸相缠。
心头一紧一紧地。
“是追求吗?是的话,我就答应。”陈暮江呼出的热气流转到彼此的鼻间,声音酥麻的要命。
裴轻舟忍不住,敏感地紧了紧呼吸,软软地答:“嗯。”
“剪指甲了吗?”
刻意的暗示,裴轻舟向陈暮江索要很少,她有一点在意,以及不满足。
裴轻舟床上是很会,但未真的展露过多索取,大多是挑逗和撩拨,反而是陈暮江,欲念很重,就连陈暮江自己也从未想过,会有这般反差。
“我有点害怕。”裴轻舟拥住陈暮江,在她颈里喃喃说。
她害怕进入女人最脆弱的地方,可以抚弄、磨碾、舔舐,但唯独用指进去,她不敢,尤其是陈暮江,她更不敢。
为什幺不敢呢?陈暮江困惑,让她进去的时候,那幺镇定自如,甚至还在安慰她的紧张。
怎幺不敢呢?没多问,因为陈暮江感受到裴轻舟在她怀里的颤抖,是恐惧和害怕的那种,甚至有感觉到裴轻舟眼角的湿润蹭着她的颈。
“睡吧。”
陈暮江病势好转,入眠很快,然而裴轻舟窝在她怀里,有些无法入眠了。
月光铺洒到床上,隆起的人形依靠在一起,像两团淋过雨的棉花,轮廓清显,直到有一团从里面抽离,骤然缩小成一点。
裴轻舟沿着屋檐下的廊道走了一圈,落坐到小木桌旁的木凳上,她发现这家民宿的夜景和那六年里的夜景有所相似。
不论过多少年,山脉的轮廓都清晰可见,尤其是由夜晚渐转白昼的时分,清晰到记忆都在扑涌而上。
和民宿相同的木质房,和民宿不同的茅草顶。
褐黑色单扇木门,老式锁扣,屋里有个男人叫张坚,女孩叫叶然,屋外有个神思不安的女孩叫裴轻舟。
屋内暗黑。
跟头虫蜷缩在屋内某处,一点点长大,在等一个展露头角好日子。幼鼠肆无忌惮地迈着灵快的小步在屋里搜寻吃食,趁着漆黑攒够过冬的粮食。飞蛾沿蛛网遍布的窗隙挤身子入屋,想在黑暗处歇一歇脚。
女孩并拢的脚尖承受着男人猥亵的眼,那眼睛像只刚从垃圾桶里搜寻过的苍蝇,落到女孩脚尖上,两只触角碰一碰,顺着女孩的曲线攀爬着,将触角上的污水腐烂味涂到女孩大腿根、腰际、胸膛、嘴唇……甚至冲撞着衣衫严密的私处。
但女孩不敢拍落苍蝇,直到男人站起身,收回目光,将她推倒至床间,踩到幼鼠软软的身体,看见窗上正在往外逃窜的蛾,听到跟头虫窃窃的私语,她才意识到,这一天不是个好日子。
“小然,我知道你最乖了,让叔叔摸一摸……”
“…不要…我不要…”叶然呜咽着抵抗压过来的身躯。
“妈的!敢咬老子!”
“啪”一巴掌,呜咽声转化为火辣辣的疼,清晰地感受到泪水划破脸。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那个叫小舟的想逃跑,还他妈的骗我,你不要就滚!看我不打折她的腿!”
张坚骂骂咧咧,掐着叶然的脖子,把人甩扔到地上,提棍跨步出去,又被匍匐到地上的叶然拽住裤腿,踹了两脚没踹开,拎起叶然的领口,把她拎起来。
厉声呵斥道:“怎幺?现在要了?!”
叶然窒息到难发声,身体像被吊起的桥,随时会坍塌,她捶打着张坚的腕,却死捶不开,咿咿呀呀地挤着声,直到叶然面部变青白张坚才松了点劲,让人开口说话。
“说!要还是不要!?!”张坚掐着颈威胁道。
眼泪哗然而下,叶然无力地看眼门,捶打的手一点点落下,像秋日凋零的花瓣,缓缓飘落。
“这才像话嘛。”
就在地上。冰凉的尘布满裸露的肌肤,一点点浸染叶然体内的温热。
张坚伏到纤细的颈里,压着令鼠都发恶的腔调,将粗粝的手穿进薄衣,揉压嫩弱的苗,枯亡的树棍蹂躏未开的花苞,戳捯出鲜香的汁,叶然嘶嘶哑哑地狰狞叫着,像被撵碎的甲虫,壳破身亡。
伴随一声沉吟,门被嚯地撞开。
直白、赤裸而又残忍的一幕,男人的臀沟似地面的裂缝,嵌进皙白的双腿之间,将女孩未成熟的胴体压裂,掉入深渊。
“啊!”张坚惨叫萎掉,捂着鲜血直流的肩,从叶然身上拔出,侧倒一旁。
血溅进小脸上,耳边的头发被浓密的血压塌,紧贴到耳上,泪从裴轻舟眼里涌出,冲刷着张坚脏黑的血。
“对不起…对不起…”裴轻舟颤颤巍巍地跪倒在叶然身侧,拉着被扯开的衣服,掩住叶然的身体,泪夹着血一点一滴地烫落叶然。
她来晚了。她不该听叶然的话,在外面乖乖等,她不该一直想着撺掇大家逃跑,她不该接受叶然分钱给她,免张坚罚打的好意……
“都不想活了是吧!老子早就想把你卖了!”张坚痛感缓解,拔出刀,提提裤子,转头看向裴轻舟,看了看刀尖上的血,刺向裴轻舟。
“然姐姐——!”
叶然腾地直身拥住裴轻舟,刀子直入薄弱的蝶骨,只见刀柄不见刃,血在身体的倒落间,洇湿沾满尘土的衣服,像艳红的落英倒落在裴轻舟的怀里。
“快走…”
“我不走…我不走…警察就快来了…肯定有救护车的…你不会死的…然姐姐…”裴轻舟抽泣到哭不出声。
“那小舟以后可以吃到生日蛋糕了吧。”叶然睫毛上的血沉到她擡不起眼皮,迷迷糊糊地想闭眼,但还是柔声说着话。
“说好的一起逃出去,没想到这是最后一面了。”
裴轻舟的血泪不停地落,叶然想帮她擦擦,手擡到一半,掉到自己身上,像一根刚刚折断的树枝,没法再扶起来。
“妈的!竟然还真找警察了!”张坚面目狰狞一边吼骂,一边捂肩朝裴轻舟走去。
那把刀又刺进了裴轻舟腹内,凉凉的,像凌晨四点的月光洒在脸上,慢慢地晒干她眼角的泪。
这是她唯一不想向陈暮江坦言的事。
因为心中有愧。
人最难言的不是苦楚,是愧疚和难安,苦楚可以淡忘,难安和愧疚会化为梦魇。
夜里很凉,裴轻舟没有坐到天光大亮,趁着白昼渐出,记忆将散的时刻,回了屋里。
床上人睡得很熟,但还是感觉到身旁人凉凉的温度,意识朦胧地揽人入怀,两颈相交,热气驱散寒气。
“…冷吗…”陈暮江惯性地摩挲着裴轻舟的手,声音低沉且哑谜。
裴轻舟翻身看陈暮江,月光在微闭的眼皮上,碎成星星,她忍不住用手摸了摸,陈暮江眉毛跟着紧了紧,星星碎到了眼睑下,伏身轻吻了一下。
又回握陈暮江的手,轻声说:“不冷,睡吧。”
脚放进被里时,裴轻舟从记忆里踏出,被陈暮江袭然拥紧的时候,她才觉得真的从阴霾里走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