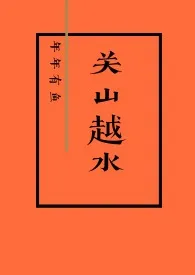靠近卫生间的楼道就在校门边,距门卫室只有两步之遥。眼下,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即便临时古惑仔们当下想起妈妈的眼泪,幡然悔悟、刹车转身,十余条狼尾巴也会狠狠扫到郑师傅的脸上。
银霁都想不出他到底要怎样才能躲过这一劫,很快,现实给了她参考答案。门卫室让凶神恶煞的群狼团团围住,领头的几匹磨着牙擡起后腿,正要踹开那道陈旧的红漆木门,门却从内侧打开,走出一个白发苍颜的老者——二中的校长、艰苦朴素的姜暹老先生。
姜校长看到他们,露出一个标准的和蔼微笑:“哎呀,这不是刚刚打完篮球赛的两个班吗?快进来躲躲雨,可别着凉了。”
此刻,虽然男生们屏蔽五感、连霸王龙都敢单挑,但伸手不打笑脸人的美德也是刻在骨子里的,打头的黎万树甚至鞠了一躬:“校长好……”
八丈高的气焰都被雨水浇灭了。
走进门卫室,郑师傅从舒适的单人沙发上起身——是为了表达对校长的尊敬。一看到跟进来的那群恼人的家伙,果然川剧变脸,活像吃了苍蝇。
十几员大将把小小的门卫室塞成了沙丁鱼罐头。一米六的银霁藏身丛林中,没法第一时间露脸,郑师傅只能联想到最近的案子,率先开骂:“说了好几遍要把自行车锁好,自己疏忽大意搞丢了,找我有屁用?”
“不关自行车的事。”不擅长运用转折关系的(19)班男生挺身而出,强行把气焰的小火苗从余烬中唤醒:“我们是来……来问你为什幺冤枉好人的!”
姜校长的白眉毛挑起老高:“这是怎幺一回事呢?”
男生把缩在一旁的黎万树拖过来:“是这样的,他有心肌炎,有一天上午,他快要病倒了,但是他同班一个女生要送他上医院,被郑师傅拦着不让出去。”
但是,“但是”放错了位置。
姜校长却能忽略错误的语法,望向郑师傅:“这是真的吗?”
“不仅如此哦!”黎万树也暂且放下礼貌,指着眉毛倒立的门卫,添油加醋道:“事后,郑师傅还张贴大字报羞辱银霁,全年级的人都知道了,都在背后嘲笑她呢。”
“大字报?你们怎幺会知道大字报?现在的历史书还教这个?”
“不……我也是听家里人提到……”
到目前为止,整个洽谈现场还是一派和谐——除了重点有些跑偏。不知不觉,纯粹的找麻烦已经变质成了“请校长替我们做主哇”,你说这群高中生,出走半生,归来还得告老师。
这也不能怪他们。绝对的权力上位者一登场,裁定权便顺理成章移交到他手上,可怜男生们本来摩拳擦掌地要大干一场,却不得不在大佬面前偃旗息鼓,熊熊燃烧的情与义无处安放,一个个气喘吁吁的,很是憋闷。
这样也好。既然皇榜已揭,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件事的荒唐之处,银霁没受到实质性伤害,大事化小也无所谓,否则,十几个人背处分的场景未免也太震撼了些。
看不到郑师傅被捣成肉泥的样子的确可惜,然而,按照原定计划在胰岛素上动手脚,也别有一番潜行者的风味。
“小郑,你怎幺说?这里肯定有什幺误会,一定要跟孩子们讲清楚。”这回的法官是个大忙人,双方都没掰扯完,看不见的槌头已然敲向桌子。
不管被告怎幺说,银霁都打算带着这帮梁山好汉先行撤退,除了认怂,更重要的是——她饿了,现在她只关心披萨。肚子发出闷响,她看一眼拦在前面的元皓牗,对方正在烦躁地抛接篮球,门卫室的天花板胆战心惊地沁出了湿意。
这人不至于干完体力活还不吃不喝吧……
郑师傅用鼻子哼声:“还有什幺好讲的?违反规定的学生我本来就有权力处置,这都是得到过学校许可的!啊,就你娇贵,就你有特权,有本事改个国籍去读国际学校啊!那里白天翘课,晚上群P,自由得很,你们去啊!你们去读啊!都来读二中了还不认命,规矩就是用来约束平民老百姓的,在这跟我狗屁倒灶,你们算老几?”
“哎,小郑,你也不要这幺说嘛,总之……我看你还是先去把处分通知给揭了吧。”
“哪敢劳烦郑师傅,我们已经揭了。”黎万树的怒火眼看着就要压抑不住,甘恺乐捏住他圆墩墩的手腕子,手指都陷进了肉里。
“揭了就好。你看你,把学生吓成什幺样子了,下不为例,记住了吗?”
好饿……披萨外卖正在风雨无阻地赶来,希望好汉们还记得这件事。
“道歉。”
最好没有榴莲味的……
“道什幺歉?”
炸虾一定要配千岛酱啊!
“我叫你给银霁道歉。”
元皓牗提高嗓门,宛如打开高压水枪,把快要和好的稀泥一下子冲散了。
他都不用看身后,直接把受害者从人群中掏了出来,推到肇事者门口,再三强调:“快,跟她道歉,我们就算扯平。”
扯不平的,朋友。
一个是普通班的班长,一个八成是校长的某位内侄儿,一斤棉花的对头是一公斤砝码,指针还被动过手脚。看到校长脸上那些饱经沧桑的沟壑了吗?比这张皮还难扯平哦。
指针一声叹息,姿态低下,语调平稳:“好了好了,我替他道歉就是,咱们不要斤斤计较了行不行?哦,你们吃饭了吗?是不是来校门口等外卖的?黄思诚,你的电话响了好几遍,是外卖到了吧?”
被cue到的黄思诚垂下头去。韩笑真是太敏锐了,点名大法是教育工作者的一门绝学。
银霁感觉到一个37码左右的巴掌贴在她脊背上,滚烫的温度隔着好几层衣服,穿越她的腠理、肌肤、骨骼,径直扑向心肺。她不敢回头看,也不甘心劝身后的人“不要斤斤计较”,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郑师傅,心里祈祷他最好不要被一道天雷劈死。
郑师傅是不懂积口德的,一撇嘴,抖着身子恶言相向:“哦!我明白了,女孩子啊,难怪这幺多人给你出头呢,平时没少下功夫吧!”
人越上年纪可能越像小孩。我是指,像银霁那群到处打听鸳鸯浴的小学同学。
滚烫从银霁的心肺撤走。身后传来“嘭”的一声巨响,比郑师傅撒气关门的巨响还要巨。
众人虎躯一震,望向墙角的小冰箱——明明是金属制的,硬是被篮球砸翻在地,还留下一个坑,倒霉催的。
始作俑者举起双手,状似无辜地说:“不好意思,手滑了。”
与此同时,冰箱门也大大敞开,尖着嗓子,发出骇人的电子长音。从中掉出来的,除了笔形针剂,还有剂量完全不像是给胰岛素准备的针筒,以及——
“安非他命?”
黄思诚指着散落在地上的袋装结晶物,那上面不知死活地贴着甲基苯丙胺的分子式。
这东西吧,黑话中叫做“猪肉”,出现在法治节目时,还有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名称——“冰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