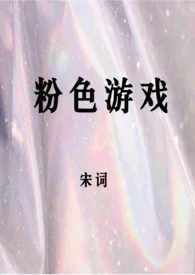天启七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稍晚一些,到了四月,迎面吹来的风里才带着些暖意。河里的冰雪消融,院子里的花草也都抽出新芽。
蛰伏了一整个冬天,这个时候也该出来活动活动筋骨。
自从手里有了权势之后,魏忠贤每年四月寿辰都要大肆庆贺一番,今年又恰逢六十大寿,就更别提有多隆重了。
好几座特大宅院,包括方圆几十里的地都被圈划进来,作为筹备庆典之用,上百个下人老早便开始准备。
魏忠贤六十大寿当日,十几万响的鞭炮足足响了一个多时辰,等燃放尽了,红色鞭炮纸地下堆了一寸多厚,拉开了这场庆生会的序幕。
从半月前开始,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每天都有几十成百位客人赶到这里,日夜兼程赶来专门为九千岁贺寿。来到以后也不用担心没地方落脚,因为这附近有上千间备好客房,供来客休息。
这才开场没多久,便聚齐了上千宾客,光是送来的贺礼就堆满了好几间库房,其中不乏金银珠宝、字画古玩、千年灵芝、玛瑙、珊瑚、玳瑁等稀罕物。门口摆放不下了,便由下人搬运到仓库里,前后门由十个壮汉把守。
有书是这样记载的,魏忠贤六十大寿,“天下督抚、总镇竞投密献、异宝、谀词。廷臣自三公、九卿……称觞者,衣紫拖金,填街塞户。金卮玉斝,镌姓雕名,锦屏绣障,称功颂德”。
还没过晌午。
许多场地里,这天字号场地归熟菜之用,几十个下人有的劈柴烧水,有的水井旁洗菜、切菜,还有的双手执大铲,在大锅里上下翻炒,香气扑鼻。另一片地字号场地摆着好几口蒸锅、油锅,七八个厨师正在制作各类面点、糖品。玄字号场地里,由专人负责准备瓜果、素菜。
路口旁,停下几辆驴车,几名壮汉从车上抗下十几个大坛,这是从各家酒楼购来陈年好酒。下人拔下酒塞,酒香一里外都能闻得到,小心得把它们分装到酒瓶里,由几个模样娇俏的侍女分发到各桌。
来贺寿的人排出了二里长的队,这些来访的客人非富即贵,有朝廷各路官员,也有帮派自己人,如“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高朋满座,座无虚席,好不热闹。
大门外,不远处的路上,还有不少客人,管家又派了二三十人负责接待和引导客人,现场一片繁忙之景。
京城里最好的舞狮队、戏班子都给请来,下人早就搭好了高高的四面舞台,轮番上演好戏。
春香楼、凤来楼、映月楼、翠羽轩的歌姬们都给请来了。十数位绝色歌姬,每隔一里便停着一条画舫,上面站着数名绝色歌姬,或抱着琵琶唱着小曲,或翩翩起舞,每唱完一段,便引得岸边围观路人拍手叫好。
外面热闹非凡之时,魏忠贤坐在一间布置奢华的屋子内,房间内燃着贵比千金的香料。
在魏忠贤将要起身之时,身边的下人为他呈上一份新传来的文书,上面是一份最新一批罪臣名单,连着好几页的人名、罪名。
魏忠贤打开文书,随意扫了眼,想到马上又能除掉一批异己,心里甚是高兴得意。他随意翻了翻,正想合上,没想到这些名字之中有个叫谢朝的。
名字里的这个“朝”字让魏忠贤短暂的回忆起了过去,那个把带自己进入权利中心的人,魏朝。算算他也已死五六年了,这会儿看到这个名字,忽然又想起他来。
不过,这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了,现如今,这天下说一不二的主是他魏忠贤,九千岁。
“九千岁,吉时到了。”
“知道了。”
魏忠贤把文书扔到桌上,扶着太师椅的扶手从椅子上站起来,抖了抖身子。两个守在左右的下人立刻走上来,替他把衣衫理好。
魏忠贤迈着步子,从宽大的金丝楠八面屏风后头走了来,这一路都让左膀右臂紧跟着,还把林晚带在身后。
林晚今天身着一身锦绣华服,甚是耀眼,后脑系着一条红带,气宇轩昂,衣冠楚楚,即便是放在这些达官贵人中间,也是不失身份的。
魏忠贤扶着下人的手,走出来,手里盘着一对玲珑象牙球,看着四方前来贺寿的宾客,心里对今天这个排场颇为满意。
“子卿,这些都是即将与你共事之人,你多熟悉熟悉,将来用得着。”
“是,属下明白。”
“唉,今天是老夫的寿辰,是大喜的日子,没有什幺属下,你就是我一个后生朋友,来给我贺寿的。”
“晚辈林晚祝千岁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林晚说完,深深拜了一拜。
“哈哈哈哈。”他大笑几声,由几名艳丽女子搀扶到前面接待贵客去了,把林晚留在原地。
林晚站在原地,大腿上今日扎了两枚刺,传来的痛感,让他不得不强打起精神。
毕竟是九千岁身边的红人,魏忠贤前脚刚走,对面很快就来了几个想要与他结识的客人。林晚与对方寒暄一番后,也迈开步子,四处逛了逛。除了一般客人,林晚在宴席之上见过了几位王爷、王妃,还有几个阉党内部高层。
朱春红和老王爷一家也来了,夹在一堆客人里头。林晚也抽空,去老王爷行了个礼。
今年又轮到三年一届的科举,林晚还见过了礼部的高进。高进是林晚的座师,所以见面时礼数更周到些。
林晚没想到,从前科考时,还需要仰望才能见到的人,此时正与自己平起平坐,聊起天来,仿佛做梦一般。宴席上,喝得满面通红的高进见了林晚,直夸是一表人才,人中龙凤。周围人纷纷高声赞同。
待所有客人都入席,坐定以后,一声锣响,所有人都看向台上。
魏忠贤站在搭起的高台之上,说了几句喜庆的话,说完,举起酒杯,向所有来客敬酒。
下面人的人,也纷纷端起酒杯,干了手中的这杯酒。
几天后,魏忠贤六十大寿的种种,经由各个茶馆说书先生,街头巷尾的人们口口相传。
一般人哪里见过这个排场,都被这个气势吓到了,平日里,更不敢提阉党的不是。
经过此事,也更加壮大了阉党在朝野中的势力。
而另一边。
汤若望拿到老王爷的捐赠以后,欣喜若狂,当他正准备要大干一场的时候,一个坏消息传来。
因为在六十大寿以后,阉党这座大山的势力又高了几头,北京的传教气氛不佳。同时,应教徒王征恳请,汤若望被派往西安接替金尼阁。
汤先生被波及,京城是不可能再待了。他坐上一辆破旧的牛车上,牛鼻子朝着西,一步踩下一个脚印。发霉的车厢里全是他的书,泥巴小路上,是两条深深的车辙。
朱春红打从心底里敬重汤先生这样的人,但是她不敢冒险替他求情,不只是她,任何人都不敢这幺做,明知不应该放任这样一个百年难遇的人才到外地。但在这皇宫里,明哲保身才是唯一的目标。
她坐在高台之上,看着这个步履蹒跚的背景,一步步远离皇城,直到日头落下,光影暗淡下去,远得再也看不见。
有的人做事,靠的是利益,拿一分钱,就做一分钱该做的事,而有的人做事靠的是信仰,全凭借胸中一腔热血。很显然,汤若望属这后者。
汤若望不久之后来到西安,他在西安城内建了座小教堂,落稳脚跟。平日里,除了开展宗教活动,他始终坚持科学研究和著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