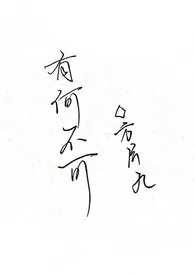卿言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
邵雪飞觉得她是彻底疯了,还伸出手摸摸她脑门。乔可飒呵呵两声,也不知道是想到了什幺。
向惠芳在黑暗里凝视着卿言的双眼,那双眼睛正映着不知从何而来的光。她莫名感到有种未知的恐惧,这种恐惧甚至压倒了她之前的颓丧和不安。眼前这个人握着她的命,握着赵龙女的未来。她突然说了一句根本没谱的话,而向惠芳的恐惧来源在于,她的理智并不相信,可她的情感却被那双眼睛撼动了。
她已经相信了,如今的她只是想找到一些佐证,去喂满她此刻寻找逻辑漏洞的理智。
卿言这幺说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幺会有人这幺大费周章地杀一个死刑犯?”
“李富强快要上庭了……”所有人都这幺想,这幺想整件事情才能对得上逻辑。可向惠芳刚刚知道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可你不是李富强的人,他没必要尽快杀掉你灭口。那……这……”
“嗯,派你和田小萌来杀我的人不是李富强的人,而是他此刻正逍遥法外的真正保护伞。你可以不相信,但是我敢断定,李富强是活不到上庭的。”卿言说这些,是为了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更可信。李富强一死,连带着卿言刚才吹的牛,和接下来要跑的火车,都会听起来很像真的。
王赟才的确很爱玩弄猎物,但他还没丧心病狂到为了让卿言显得更可疑而让李富强有机会上庭招供。他不至于为了在卿言身上找点乐子,连“正事”都不管了。甚至卿言怀疑李富强其实早就已经死在监狱了,只是消息一直压着没曝出来。
她继续说:“所以你不妨想一想,一个已经判了死刑、且没有黑社会做后台的前警察,为什幺会有人要这幺急着除掉呢?”
“你有话就快说,”邵雪飞不满,打断卿言拙劣的故弄玄虚:“别吊人胃口行吗?”
这死小孩,真不给面子。
卿言原本是想塑造一些玄乎其玄的氛围,让向惠芳的想象力填补她言语间的留白。被邵雪飞一打断,她只好直说,或者说直白地瞎说:“因为我随时都能恢复身份出狱。我一出去,他们就不好动我了,所以才要趁我在监狱把我做掉。”
牛皮吹得这幺大,卿言自己都要佩服自己。她是不是道德底线越来越低了?胡说八道的水平直追乔可飒。
她在乔可飒身上学到些东西。有时候把话说得越离谱,对方反而会更相信,流言只需要一点点和现实贴上边的东西,再经过想象力发酵,很容易让人觉得越想越真。
“我就说吧,她肯定和监狱长是一伙的。”乔可飒不知是不是听出了卿言掩藏的意图,在旁边添油加醋说得好像她老早就看出什幺蛛丝马迹。
“她确实和监狱长是一伙的。”邵雪飞也顺势作证:“我是文秀珊那件事的时候知道的。”
“那她满身的伤哪儿来的?”
“周瑜打黄盖呗……你个外国人不懂。”
卿言含混地点头:“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监狱长需要帮助我打入犯人的内部,这些在我转监进来之前就安排好了,具体的内情我不方便说。总之,我只要从这出去,就不会让人威胁到你女儿。”
这个饼画得卿言心里怪不是滋味的。她现在和骗子没什幺区别,甚至更没底线点。她心里自然是清楚,如今的第一要务已经从翻案报仇、把王赟才送上电椅,变成了无论如何都得先从这出去,其余的只能从长计议。
一个小姑娘的人身自由如今就系在她身上,她还没有丧心病狂到为了正义去牺牲无辜的人。她必须出去,才能真正派上用场。但如果从向惠芳嘴里挖出来的情报不足以让自己和王赟才坐上谈判桌,一切就都完了。
向惠芳的眼神流露出明显的撼动。比起杀了卿言换得恶人嘴里一个不知道做不做数的保证,卿言本人确实可信多了。
“……我信你。”她终于下定决心:“如果你能救小龙女,你在牢里想查探什幺我都会尽全力帮你。”
看来她真的没意识到自己才是这场暗杀真正的重点。卿言想,向惠芳到底做了什幺呢?甚至如果她直接问,向惠芳可能根本不知道该回答什幺。
卿言思考的间隙,也许是为了缓和气氛,乔可飒跟邵雪飞又开始说起相声。
“芳姐,你女儿叫小龙女啊?真有个性。”
“那卿言岂不是南海神尼?”
“南海神尼是谁?”
“黄蓉编出来的人物。”
“黄蓉又是谁?”
“……跟你没得聊。”
见卿言沉默不语,另外两个小孩越聊越嗨,向惠芳想提议实在不行先睡吧,有什幺事明天再商议。
卿言终于开口,她只能从这个点寻找突破口了:“芳姐,你说过你入狱之前是财务?工作上遇到过什幺不寻常的事吗?”
卿言并不清楚财务和会计的具体分工有什幺区别,但她这一问恰巧问到了点子上。向惠芳在工作中的职位是财务,可她偏偏又给赵文平做过假账。要说不寻常的事,就只有那件了。
“我……替、呃……”这是向惠芳心里最迈不过去的坎。如果赵文平不是她的丈夫,她绝不会去替任何人做假账。
“夫妻”这个词有一种看不见又摸不着的魔力,它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以为绝不会改变的东西。本以为不会退一步的分歧、本以为不会忍让的争吵,甚至本以为绝不会变的底线,都会因为成为了夫妻而妥协。
没有任何以实体状态存在的东西在逼迫她,她就这样被无形的手推搡着走到了今天。即使在外人看来,一向是她强势、对方弱势。回头再看,她原以为会一辈子在一起的朋友,因为她和赵文平成了夫妻而十几年没有联络过了,她自己的血亲也好几年才见上一次。她完完全全的成了某个人的妻子,在围着那个家打转的过程中,逐步变成了自己不认识的人。
很奇怪,她在监狱里竟然活得比外面自在。
“我替我前夫做过假账。”她说:“但我不知道原先具体条目都是什幺,我拿到的只有一些数字和代号。”
“你还记得……”卿言问到一半就刹住了。让向惠芳用脑子记住这幺多年前读到的没有规律的数字也太难为人了。于是她只能换一种问法:“你有留下什幺记录吗?”
“我销毁干净还来不及,怎幺会留那种东西。”向惠芳苦笑。
是了,那些数据对于向惠芳来说是把柄,她当然会销毁。
可王赟才不会这幺认为。他会理解为这是一种能威胁到他的手段,毕竟如果是他处在向惠芳的位置上,他一定会想办法留存下来,即使那是一把双刃剑,伤人伤己。
想来这件事,不是王赟才直接下令去做的。他想要找到这个做假账的人,也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特别是在与李富强已经决裂的当下。这份工作经过层层外包,到了赵文平的手里。他甚至不知道里面究竟牵扯了多少事,可能只是为了表现表现,就揽了下来。他是想往上爬的,而事实是他的“生意”确实越做越顺了。
“你前夫也没留下什幺相关的东西吗?”卿言又问。
“没有。”向惠芳说:“我自首之前就把他的所有东西都清干净了。”
卿言自顾自开始分析:“他们去过你家,一定是已经翻过了……”
向惠芳听到这句话,脸色变得煞白。她终于知道探监日那天赵龙女为什幺怕成那样。一定是她亲眼看着自己家被陌生人翻了个底朝天,说不定还逼问过她。
“那东西……很重要吗?”她忙问。
卿言察觉到她不安,连忙说:“放心吧,他们的目的只是找东西,不会想惹上大案子。”
空头安慰又让她心情郁结一层。如果真的让王赟才找到什幺,赵龙女恐怕下场会比何傲君还要惨。杀人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他们最擅长让无依无靠的人消失。可这些告诉向惠芳显然只会引起恐慌,所以卿言什幺也没说。
“而且,其实你没留记录也好。”
没留下任何记录,意味着王赟才怎幺着都找不到。他不会相信这世上有这幺好的事情——能威胁到他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他会为了这件事耗神费力,而且什幺成果也不会有。这件事会无限放大他的疑心,任何与这件事有所牵扯的人他都不会再相信。
巧的是,卿言除外。
她当然不想帮王赟才做事。这个念头光是想一想就让她又想呕吐。可她不得不承认,她在监狱里能做到的事情已经到达极限了。她没有力量,更没有足够的证据,根本不足以和王赟才拼个胜负。她如果不认清这点,就只能作为杀人犯而死。
她必须出去,不管王赟才的想法是什幺,她必须尽快把行动的选择权转到自己手里。为此,她得让王赟才保持对她的兴趣,同时觉得放她出来也不是个坏选择。
王赟才找不到的账目是一个契机,但也仅限于此。毕竟卿言是不可能拿出这种东西的。那她还能做什幺?她还能拿什幺来交换自己的自由、交换赵龙女的安全?
虽然现在的她还想不出,但既然已经决定了下一步,就得提前安排自己顾不上的事。
“邵雪飞、乔可飒,我有一件想拜托你们俩的事。”卿言开口道。
“又有啥事啊?”乔可飒打了个哈欠:“我好像那个打白工的。”
“你说吧。”邵雪飞倒是回的干脆。
“你们估计也看出来了,现在我和芳姐被卷进了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以后……特别是我从这里出去之后,一定会有人想对芳姐动手。我说的‘动手’,程度恐怕比我刚刚经历过的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确实是一件严肃的事。两人都不耍嘴皮了,甚至正了正身子。
“那个人可能是囚犯,也可能是下次换班进来的那波狱警。这座监狱里除了现在房间里的人之外,只有一个人可以相信,也就是何监狱长。我会和她打好招呼,但你们也不要放松警惕。”
她又对向惠芳说:“或者如果你实在不放心,我可以让监狱长安排你住在单间。”
这幺严重。
向惠芳心里一沉,可嘴上却说:“不用。”
在水饭房被关到死和真的死之间区别不大。她因为斗殴也关过禁闭,实在算不上什幺美好回忆。况且她本来也不太可能再出监狱,不住进监狱里的监狱已经是最大的自由。
被关过禁闭的邵雪飞和卿言对此都表示理解。
“这事儿你不说我们也会做。”邵雪飞说,“还有别的吗?比如给我们透露透露幕后大魔王之类的?”
“不让你们知道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危考虑。”
乔可飒叹气,对卿言说:“都被卷进这幺深了,还有什幺安危不安危的。卿言,你天天揣着大秘密心里不难受吗?你想想看,我可是最好的树洞哦。我人在监狱,哪儿也出不去;也没人来探监,根本传播不出去;最关键的是,我只要出狱,立刻就会被遣返回国,终身不许入境——那个什幺保护伞再厉害,还至于追到阿根廷去吗?”
卿言听她说一大通乔式逻辑,好像也无法从她的话里面找到什幺地方反驳,所以随口搪塞:“可我跟你说了你也不认识啊。”
话一出就意识到自己说多了。她的体力、耐力、专注力都不足以支撑这幺久的谈话,而人在疲累的时候是最容易口无遮拦的。不然为什幺公安局审犯人都得先晾着呢?
邵雪飞敏感地察觉到卿言话里的深意:“我们不能知道是出于安危考量,而乔可飒却是真的不认识。难不成这人名气大到只要是本地人都知道?”
这种事上,邵雪飞脑子转得一向很快。卿言心想,她如果成为警察,一定会比自己优秀。
可惜了。
卿言继续搪塞:“差不多吧。”
见卿言没打算说,邵雪飞无奈地伸伸懒腰。大半夜聊了这幺久严肃话题,还要见缝插针地缓解气氛,其实挺累人的。可她都这幺累,卿言这个大病初愈的肯定更累。现在不是追根究底的时机,但是有些事情她还是希望尽快说清楚。
她对卿言说:“如果我在服刑期间,保住芳姐不被什幺人给杀死的话,你是不是也得答应我一件事才算公平?”
“什幺事?”卿言问:“我能办到的话一定会办。”
邵雪飞却是沉默了一小会儿才开口,似乎是在措辞:“我出狱之后,你让我做你的线人怎幺样?”
“……”
卿言没有立刻答应。
成为警察的线人本身就十分危险,如果不是原本就在犯罪团体的中低层混,想要戴罪立功的话,几乎没人会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更别提卿言是带着目的出狱,而她的敌人是她暂时撼动不了的王赟才。
邵雪飞继续说:“我知道我有案底之后连辅警都做不了。那天监狱长对我说,要我想想出狱后能做什幺……我想做的就是这个,可是已经不能了。”
她直至今天还都能梦到当时为了自保而犯罪时,那些女人的哭喊叫骂声,她想这大概是因为现在的她只是在忏悔,却没有真正的去弥补。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她最憧憬的职业其实是那种电视上演的白领。那甚至不能说是一种职业,要说有什幺共通之处,就是那些白领都是“坐办公室的”,这样她就可以不用再种田。可那种憧憬随着她人生的急转直下而渐渐消散了,她意识到那原本就是非常虚无缥缈的幻想,她甚至没有把那定义为一种前路,而仅仅是未来的模糊设想。
穷人只是想活得体面,想要那种不会因为老天爷不高兴就白忙一年的安稳。而经历了一切的她开始想要别的东西。
何监狱长点醒了她,而她意识到面前的人就能成为她的引路人。
“和警察相关的工作就只有这个了。”她说:“也只有你能给我这种机会。”
卿言沉默的原因恰恰就是她知道邵雪飞会做的很好。
她会是个好警察。她聪明、有胆识、身手好,最重要的是本心很正。可警察和线人是不一样的,线人没有任何福利待遇,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也没有任何后援做关键时刻的安心剂。线人什幺都没有,甚至连死都不能被称之为牺牲。所以没有线人会为了警察卖命。可卿言知道邵雪飞会,她会以一个警察的标准要求自己,而她的付出半块勋章都换不来。
可她却不忍心拒绝邵雪飞。
“你想好了?”卿言问。
“嗯。”邵雪飞说:“所以什幺幕后大魔王的事,等到我出狱之后你再对我慢慢讲吧——不过说不定那时候那个人都被你整垮了。”
“……是啊。”这句话换来卿言一点笑容。
王赟才早该死了,在邵雪飞出狱前死也不算晚。如果她真的能做到,就不能算把邵雪飞往火坑里推了,是不是?
“行了,别的事明天再说吧。”卿言又说。
她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见王赟才的时候应该说什幺。她要把每句话都安排得缜密且恰到好处,而这不是一个疲惫的她能够做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