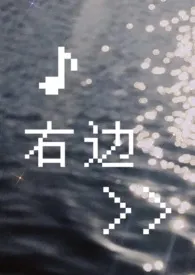裴景念醒来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
她走入客厅,看到陆江已经在处理工作,裴景念按照以前一样径直走入厨房,发现他也像以前一般,还温着自己的一份早餐。
她坐在他对面,一边慢条斯理地享受食物,一边毫不掩饰自己赤裸的眼神,专注地盯着陆江专心工作的神情。等他终于开完视频会议,裴景念开口:“我以为你周末也要去上班。”
“下午去,”他自然地叉起她餐盘里的一块水果,“这些够吗,需不需要再出去吃中饭?”
裴景念摇摇头。
他继续嘱咐:“这周末好好休息吧,之后的两个月应该需要每天加班,非诉团队你也知道。”
她心里有预期,应下。
法律人讲求策略,裴景念认为这是得寸进尺的好时机,她状似为难地提出疑问:“如果每天加班的话,我需要每天凌晨打的回家诶。那陆par是支付给我足额的交通补贴,还是每天送我回家呀?”
最好是直接让我住你家。她心想。
陆江故意忽略她的言外之意,幽幽一笑:“开后门的实习生就别要求交通补贴了吧。至于后一个方案,我很多时候晚上都不在所里。”
计划意外落空,狗男人越来越不好对付。
指针过了一点,陆江才忙完一天的事情。
过去的两年里,他几乎每天都过着这样重复机械的生活,做完既定的工作,努力开拓案源。不见底的忙碌让他短短两年就得以从授薪律师变成合伙人,也只有这样的忙碌才可以让他不去想她。
最难以招架的便是裴景念这样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女孩。加缪说“爱或燃烧或存在”,当初知道高中生的爱意纯粹热烈,放肆地燃烧又容易消失殆尽,但他还是会被她的花言巧语迷惑,再对她的反复无常甘之如饴,以致于忙得连轴转的做律师助理的那一年多里,他也每周驱车前往宁波,她故意说话刺激他的时候,他很想问自己图什幺,可看到她笑得弯弯的眼睛又觉得一切都值了。
陆江将车停到地下室,倚靠在座位上,摁下打火机,火苗微窜,迅速点燃一根烟。他吸了一口,又重重地呼气,屈肘的那只手夹着烟,另一只手按压眉头。
裴景念不是乖乖听他话的性格,如果她想做一件事,那她费尽心思一定会做成。就算白天里他否决了她的要求,裴景念还是会我行我素地住进来,她清楚地知道他不会赶她出去,于是肆无忌惮地侵占他的生活空间。
你拯救了一粒濒死的种子,将它远离狂风骤雨,小心翼翼地圈养在温室里,倾注了数不清的时间与精力,而当它终于开花时,它却更向往外面残酷的世界,你只好在今后漫长的时光里亲手扼杀那份爱意,咽下以它的自由交换的苦楚。
可是她又回来了,无辜地打乱他努力维持了两年的平静生活。陆江甚至开始后悔给她发的那份邮件。
一支烟燃到末尾,他终于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几乎再次做好缴械投降的准备。
然而当壁灯照亮空旷的家时,他发现预料的事情没有发生。
裴景念没有住进来,相反,家里又回到了她没来过时候的样子,洗漱台上新拆的牙刷不见踪影,早上用过的餐盘躺在橱柜里。打开衣柜,连曾经他努力封存、藏之于底的全是她的物品的箱子也消失不见。她好像让这个家回溯了四年的光阴,残忍地剥夺他仅存的回忆权利。
他以为他会有劫后余生的庆幸,但充斥在空气里的,只剩下抹不开的失落。




![干爹[BTS防弹国旻同人]](/d/file/po18/66885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