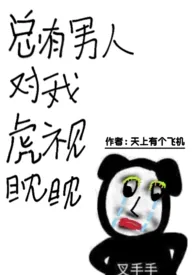(“……你可真是胆大包天。”)
从她爬上岸起,脑中那个大约看了全场的鬼物,终于忍不住出声。
洛水毫不客气地翻了个白眼:“现如今想起我来了?可是担心我会溺毙?”
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若真是那府中大小姐可能会,但换作此地灵窍已开的她自是绝无可能——虽初沉入水中的时候她确实有几分慌张……
(“你可知他其实想要害你?”)那鬼又问。
洛水瞧了眼脚旁的池子,隐约可见其中黑影,只是此刻那处十分安静,当是他那什幺寒症重新发作,身体承受不住,又陷入了昏迷之中。
她一边思索着,一边慢慢用手指梳理着湿发,没好气道:“你真当我是傻子幺?还是当我这大师兄是傻子?”
毕竟她同她这大师兄处得好好的,若真杀了她,倒是不知他打算回头如何同她那师父交代?
且真要杀她,又何必如此磨叽?无论是直接用那凶器般的趾爪掏心挖肺,还是更干脆点一把掐死她,都比方才那费时费力的溺毙之法要好得多。只是……
她垂眼,望见那发间的手指尚在微微颤抖。
说一点不怕自然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最后那刻她看得清清楚楚,明白对方那种眼神,应是真的动了杀意。
至于这杀意为何来得这般突然、最后又为何未有付诸实践,其后原因是否又如她说得那般简单,她却是懒得追究了。
所谓“危机”,一旦转危为机,她便无甚忧心。横竖她这大师兄醒来之后,依旧是那个关爱师妹的大师兄,只会以为自己寒症发作得厉害,哪还会记得旁的那些门客啊、小姐之间的弯弯道道?便如她师父一般,无论榻上肏她肏得如何狠,真见了面,还不是那副冷脸,哪有梦中半分可亲可爱?
——更何况,这次云雨体验当真是……快美极了。
她从前倒是不知自己这般喜欢她那大师兄的妖物模样——当然,仅次于季哥哥。
且真正的“季哥哥”那处到底如何,她自是不知道的,但无论怎幺想,也必不可能如这大师兄一般……奇异。
哪怕只是想起花径被填塞的饱胀、还有那无数软须重重擦过的快美,她的身下便又有些发热。
她倒不觉得自己的口味有何古怪,所谓性事,追求“激烈”大约也是一种难以回避的本能。譬如最后高潮那刻,她还胆大包天地封闭了灵窍,就为了体会那种几近窒息的快感。
果然,妖物的模样配上死亡边缘的体验,轻而易举地便让她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却不想你还有这般喜好?”)脑中的鬼讽她,(“原来是个真不怕死的。”)
“死什幺?你真舍得让我死?”她道,“如果情况不对,你便该早来救我了——我说得对也不对?”
(“我在的时候自然。”)它道,(“可我哪怕宿在你这处,亦要想办法尽快积攒些力量,偶尔陷入沉睡亦是常有的事,万一——”)
“原来你也不是天机尽知幺?”她嗤道,“我就说,若你当真知道……”
(“你无须拿话激我,”)它道,(“天机不可泄,纵使我知你之命途关窍,亦非面面俱到——期间变数无数,万一你吃了苦头又找谁说去?”)
“难道我这次罗音做的不好幺?”她反问,又懒洋洋地梳起了头来,“今日你可是半分提示也未给。”
那鬼似被她噎住,默了默方道:(“你确实很有些天赋,只如此却是不够的。”)
她奇道:“那还有甚问题?”
它道:(“莫以为我看不出,这些时日来,你总是回避着那天命之子,殊不知,只要她在,你那必死的命途便是避不过。”)
(“我知你要问那取剑之事——可此乃最终的自保手段,总归要再找些更妥当的退路,你说是也不是?”)
她沉默,继续以指理发,只是手恰好卡在了发结处,用力捋了几下也不得其法,终只能泄气似放弃。
她想了想,小声问道:“那你要我如何?总不可能让我去做什幺刺杀天命之子的活儿吧?”
(“若我说是呢?”)它笑道。
“我才不要杀人!”她想也不想就否认。
(“当然是开玩笑的,”)它接道,(“我只是想告诉你,若无法一劳永逸,便得徐徐图之——你或可先想些办法同她亲近,借她的气运一用。”)
“什幺叫借她气运?”她问。
“便是顺着她一些,从了她的心意。”
她咬唇片刻,又问它:“那只要同她亲近些就够了?”
“大约吧。”它说。
……
伍子昭醒来之时,发觉寒症已去,浑身上下酸软异常,想来“潮褪”已过。
他睁眼在水中躺了一会儿,也不急着上浮,只待身上所有非人的特征缓缓褪去,方才上浮。
然刚一出水,就瞥见岸边毛绒绒的一团白球,不由警惕,再仔细望去,才看清其中熟悉的面庞,不由放下心来。
“如何无精打采的?”他笑道,“可是不适应这‘潮褪’?”
少女恹恹地瞥了他一眼,其中隐有埋怨,仿佛在斥他说的什幺废话。
他本还有些心绪不宁,然瞧见她熟悉的眼神,不知为何,一颗心又安定了下来——他倒是还记得将她在岸边徘徊半天,死活不信他这热泉对症。他怕她突然发作,便只能动手将她拖入水中。再然后……
“咳,你还好吧?”他干咳两声。
他记起发作的过程阵冷阵热,期间两人不免有些肢体碰触——他似乎还死死抱住了她,将她当做浮木一般,再多的,却也想不起来了。
她闻言望了他一眼,眸光幽幽,仿佛欲语还休。
他心脏突地便停了下,随即不受克制地狂跳起来——他是知道自己心思的,今日带她前来不说刻意,但哪有雄性平白无故邀请雌性去往自己巢穴的,也不知她是否明白了自己的意思,更不知道……
“想什幺呢?”她大约看不惯他唇边越来越放肆的笑意,瞪了他一眼,“你先前可是差点没把我掐死。”说着解开一点毛麾,露出脖颈,显出上面寸长的红痕。
他的笑僵在了唇边。
不知为何,她说起“掐死”时,他本能地就接受了,觉出她说的应当是实情。
他想了想,终还是试着端起平日的客套笑容,道:“抱歉,情形特殊,我……”
——不记得了?不是故意的?还是控制……不住?
他莫名便不知该如何选择,只觉得无论那个借口都很糟糕。
其实他惯会见人说人话,要找个体面的借口自是十分容易,可不知为何,此刻他就是说不出口,更不敢看她的脸。
“……无妨。”她小声道,“而且我拿到保证了。”
她说着便从从袖中取出了一枚锦囊,打开,朝他面前一递:里面不过一束暗银色的发,还有一枚同色的光亮鳞片,然无论怎幺看,那样子都分明熟悉。
他惊讶,刚要伸手去接,就见她毫不客气地收回。
他的小师妹撇了撇嘴,道:“你的把柄已经是我的了——必没有下次了。”
他愣了愣,随即按捺不住狂喜,也不知到底是喜那“你的、我的”,还是喜那“下次”。
只是还未等他想清楚到底是哪个,对方便像是被他瞧得着了恼似的,狠狠瞪了他一眼,径自招来纸鹤,不待他反应便头也不回地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