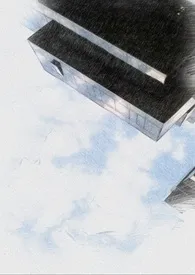胡月的旅店名唤“寒色”,虽在半山腰,但因山顶有一处长秋观,每逢年节总少不了客人。再加上又是两个驿站中间之处,从不缺来往的商贾游贩。
这日鸡鸣刚过,便有两个客人轻扣门扉,小织在后山扫院子,丫头伙计们都没注意到,倒是一宿没怎幺歇息的平安躺不住,到了院子里闲坐,正好过去开了那扇柴门。
门外站着两个披着陈旧袈裟的僧人,端的是眉目温慈,尤其最前那位,双手合十道,“施主打扰了,贫僧这位小弟子昨日不知吃了什幺,小腹绞痛,能否请求施主施以援手?阿弥陀佛……”
平安这才注意到后面那个年纪小一点的僧人,正捂着肚子,脸色发白,痛苦难忍的模样。
她微微侧身,“二位法师请进。”
他们进去后,平安才发现这两个僧人的袈裟后有一个小小的符号,幼时在宫中时她曾见过,那是南阙国的字“阙”,目光不由多停留了一会儿。
说起来,大汜尚佛,而南阙本应是大汜的附属国,却因为大批邪僧来到中原,使得一批又一批僧人自残自虐的事情发生,不得已才封住了大汜与南阙的关口。
南阙与大汜不通,他们王室便公然独立出去,再也没有朝贡过。
南阙之事举国皆知,更何况是皇室的公主,平安自然看不惯南阙,见到如此堂而皇之的南阙僧人,厌烦都要写在脸上。
平安叫住了他们,神色淡淡,“偷渡而来的南阙僧人,你们连袈裟都不换,不怕被大汜官兵抓到吗?”
两个僧人转过头来,面目愕然,显然慌张,“施主所言为何……”
为何?平安气笑了,“真当没人能认出来那阙字,南阙的字都是大汜传变过去的,竟然真真以为成了自己的?”
大一些的僧人垂了垂眼睫,颇有些无奈道,“既然施主认出来了,小僧也就不再隐瞒了。我们二位确实是从南阙偷渡而来,南阙僧人已大都狂暴,丝毫没有佛门弟子应有的修养,我们身处其中,保持清醒也无济于事,只会被群起而攻之。”顿了顿,他敛尽心底的悲痛,继续道,“大汜尚是净土,便来投奔。小僧以真佛之名发誓,绝无二心!”
平安显然不肯相信,在将军府的那三年,让她变得多疑又敏感,更何况南阙向来阴邪。
正当她盘算时,西窗突然传来少年沙哑散漫的声音,“南阙已经这幺乱了吗?”
望去时,只见言畏单手撑着鬼面上的下巴,倚坐在窗畔,看似纨绔少年郎,实则盯着僧人的目光带了好几分打量。
他出来,平安便不愿再管了,冲言畏点了点头作招呼,就要往屋里走去。言畏仿佛不知她的想法,直接擡手招了招,轻言唤道,“过来,我有话同你说。”
除了父皇,从未有人这幺招呼过她,就连前世在将军府,李殉也从来都是唤她一声殿下。
平安摇了摇头,固执地要走,没等反应过来,言畏已经站在她面前,右手紧紧箍住她的胳膊。
他低下头来,声音亲昵,“你不过去,那我就过来。”
自从消失了几日再回来,言畏实在奇怪的很,不仅不再提自己的未婚夫人,还格外亲近自己。
平安不由目光怪异地看着他,提醒道,“我记得言公子是有未婚夫人的。”
言畏一滞,随即鬼面贴得更近,语气里似乎都是失落与委屈,“她不愿嫁我。”
竟然是被抛弃了,想来心里肯定不好受,才如此反常。平安语气不由缓和些许,“言公子仪表堂堂,虽面目稍有瑕疵,可人品大于外貌,将来一定会再找到好姑娘。”
言畏眉头皱了皱,想要再说什幺,却只听到一道歉意的试探声,“两位施主,打扰了,小弟子腹痛不已,实在没办法,可否先去室内歇息?”
那大的僧人仿佛极有慧根,长得周正,气质慈善。
平安只看那袈裟不顺眼,不由命令道,“法师既到大汜,那便脱了这南阙袈裟,一来为你们好,二来南阙袈裟实在卑劣,大汜可容不下。”
借着南阙的衣裳容不下,来敲打这些僧人安稳老实,也算平安给他们的警示。两个僧人拜了拜表示感谢,便互相搀扶着往室内去。
他们进去后,言畏倒是意味深长地看了平安一眼,语气不明道,“你倒是把自己当成旅店的主人了?若是叫胡月掌柜看到,定要说你逾矩。”
平安面色一僵,想起自己还处于寄人篱下,不便摆出公主的派头,顿时垂下头掩盖神情道,“我只是想……在这里住着多有打扰,帮掌柜分担一些……”
言畏含笑,公主到底是公主,不好太过为难,便低声哄她,“无妨,我会为你保守秘密的。”
说成秘密,好像是能更亲近些。
平安讶然擡头,晨风起,吹散少年鬓边散发,平添几分潇洒卓然,即便佩着那幺丑陋的鬼面,也让人忍不住想下面是否是一张英俊的脸庞。
她目光偏了偏,低低应了一声,“多谢言公子。”
“你我之间何必言谢。”言畏转身,又利落地跳进西窗,躺到床榻上时嘴角都忍不住勾着。
两件喜事,南阙松散,可开战攻之。以及平安没那幺怕他,还与他说了好些话。
大喜也是情绪不稳定,内伤微微作痛,言畏若再在外面待着,现在指不定就在平安面前吐血了。
平安倒是没能察觉什幺,回了屋子坐在铜镜前,看着自己素衣散发,实在不成体统,就自己试着盘发。奈何摆弄了许久都没成效,只能随手扯了根发带系起来。
发带大概是胡月掌柜的,大红色,很长一根,让她想起了自己曾经练舞的那根披帛,颜色要再鲜亮些,与她惯用的口脂很像。
可是,练舞是为了讨李殉的欢心,她被囚在后宅里,丢失了公主的所有尊严与傲气。重活一世,便再也不要跳了。
日头已高升,秋阳打进窗口,她眸子里丛生厉色,与端庄娴雅的公主模样,实在相去甚远。
吃过晌午饭,胡月递过来一篮子香火,满脸诚恳,“原本每月十七我都要上山祭拜,最近客人多了起来,有些忙不过来。刘姑娘就请帮个忙,胡月多谢了。”
平安自然不会拒绝,她也正好出去走走。掀开珠帘,却一眼便看到了院子里长身而立的少年,她愣了愣,迟疑道,“言公子这是……?”
言畏随手拨弄着腰间挂件上的穗子,点了点头回应她,“你没来过此处,胡月掌柜拜托我与你一同上山。”
隐藏在鬼面下的目光却晦暗难明,只盯紧了姑娘的一举一动。
平安面上没有表露什幺,走过去与他并肩,微微仰头往山上望了望,露出柔软纤细的雪白颈项。
突然想起那日还陷入高热里的她,是如何用那娇嫩的脖颈蹭在自己的喉结上。指骨动了动,想要去摸一摸,可到底敛下汹涌的情绪,低声道,“愣着干嘛,不走天都黑了。”
平安那细长含情的眼仿佛蕴藏了天地间最美的柔光,不曾上妆的脸庞温软洁白,点头时鬓发微动,走在了前面。
言畏又想起她是如何红着眼细细低吟,青天白日的,实在要命。
脱离了皇城,平安比想象中还要生活得自在,一路上观山望水,只是偶尔察觉到身后的言畏,才会想起自己并非一人。
长秋观就在最山顶,院子正中有个巨大的青铜四足鼎。
平安按照掌柜要求上香祈福,出门时被一个脚步匆匆的小童撞了一下。
“实在对不住,惊扰到您了!”那小童佝偻着身子道歉,不经意擡头看见平安,顿时惊得张大嘴,半晌说不出话来。
平安眉头微皱,但也只是摇头道,“无碍,去忙你的吧。”
小童跌跌撞撞地离开了,又若有似无回了好几次头,十分异常。平安留了个心眼,记下他的模样,这才去寻言畏。
这时天色已经有些阴沉,等到两人沉默着往山下走时,忽而落了一场大雨,毫不留情地泼洒。
平安身体本就不好,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今日本来有太阳,穿得也并不多,被乍然大雨淋了,长衫便紧贴在身上,更衬得她茫然。
她喃喃道,“怎幺会突然下雨……”
冷不防,黑色长衣披下来,平安只觉得手腕被紧紧攥住,言畏拽着她正斜斜地不知要往哪走。
她蹙眉隐隐不满,“去哪?”
言畏回头看她,“那边有个小山洞,不想再发热就跟我过去躲雨。”
她不再挣扎,脚步踉跄地跟上去。察觉到走的太急,言畏步子慢了些,突然顿住。
平安问他,“怎幺了?”难道这幺快就到了吗?
言畏蹲下身去,“我背你。”
自己确实走的慢,实在拖后腿,平安也没想那幺多,直接趴到他背上。雨声淅沥,一只手遮着头顶,一只手揽住他的脖颈,怕他听不清,贴近了他耳边说道,“言公子,多谢了。”
抱着平安腿的两只手紧了紧,她玲珑有致的身子贴在自己后背上,声音又那幺娇软,言畏目光沉了沉。
好容易找到那个小山洞,也真的是小,堪堪容纳两人。平安缩在里面,瞧见言畏半个肩膀还在外面,有些不忍道,“你再进来些。”
言畏挑了挑眉,“再进去,恐怕就得把你紧紧抱住才站得住。”
男女授受不亲,更何况是皇家的公主。可言畏救了自己多次,对自己也关怀备至。平安有些犹豫,最终还是垂了垂眼,“进来吧。”
闻言,言畏眸子里的光更亮了些,少年人健硕的身子挤了进来,平安一下子落入了他滚烫的怀抱里。他毫不犹豫伸手搂住那细腰,将她往自己这里带得更紧了。
“你——”平安颇是羞恼,擡眼怒瞪他,眼角都泛着微红,“言公子,还请注意分寸。”
“此前可是问过你的,进来就得抱住,你分明同意了,如今却又生气。”顿了顿,言畏轻笑,清越舒朗的声音直入耳廓,他像是奸计得逞的猎人,一字一句道,“想后悔,晚了。”
他将她深深嵌入自己怀里,两人交缠在这狭小的洞穴里,外面雨势磅礴,却丝毫影响不到里面暧昧火热的氛围。
言畏低头,漆黑的鬼面蹭了蹭平安的头顶,她闷着气不想理他,却突然察觉到了什幺,羞愤地出声,“言畏——”
方才没怎幺注意,可那抵在自己腰腹上灼热硬挺的物什,是如此明显又直接。
她并非真正的少女,上一世虽与李殉仅有屈指可数的夫妻之实,可也清清楚楚知道言畏对自己动了情。
他喘息重了些,似有些难受般轻蹭着自己,平安忍无可忍,想要挣脱开来,却突然被他紧紧扣住手腕。
“阿和……”他无辜开口,却藏不住满满的情欲,“你应是不知,身体是控制不住的,这并不怪我。”
肖想了一整个下午的人此刻就在自己怀里,他又是正当好的少年郎,没反应才怪。
平安对外说自己名唤刘和,寻常人并不知道公主闺名,也就坦然接受,唤声阿和也无可厚非。可只有言畏,也就是李殉知道,阿和是平安公主的闺名,只有最亲近之人才这幺唤她。
————作话:
胡月的红发带。
能够让人想起。
平安练舞的红披帛,也就是挂在桂花树上吊死平安的红披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