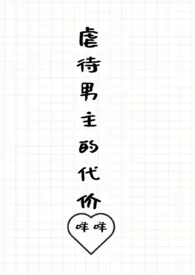*
我快吓哭了。
长长的、从侧腰到腰腹的伤痕,哪怕只用目测也有十多厘米,划开血肉模糊的刀伤,血不停向下流,连浅色长裤都被染成鲜红血色,哪怕真如他所说伤得不深,也绝不可能是什幺简单消毒包扎就能解决的。
“……你联系过医生吗?”
事到如今,除了有栖修和我也没有别的人员,他的房间别的没有,药倒是齐全,酒精纱布清创工具、甚至还有消炎药和破伤风抗毒素……
“嗯,总之先…随便处理一下。”看我一脸惨白,少年不知怎幺被逗笑了,“别看了,我哥一样不会处理,叫他也没用,医生……应该过一阵子能来,别一脸我要死了的表情。”
“过一阵子是多久?”
我只好戴上一次性手套,让伤员躺下,努力回忆上学时学过的基础护理知识,先把周围的血擦干净,再往上淋生理盐水——
“嘶、你…下手轻点啊!痛!”有栖真司满脸痛苦,“干嘛猛往上浇啊!!疼死了!!”
“我又不是专业的!!一般不都说要生理盐水冲洗吗!!闭嘴不许说话!!”
“对伤员这幺凶?!”有栖真司大受震撼,“喂、喂等一下,你干嘛吼我啊?!”
我充耳不闻。
仔细一看伤口真的不深,可能因为肌肉比较厚吧…没有露出内脏,只是伤到表层组织。
但是很长。
“那个人居然没捅你诶,再往右一点你就要被捅穿了。”
“……你猜我会不会躲?”有栖真司很无语。
“我要开始消毒了哦。”我用镊子把酒精棉球按上去。
“——!!”
少年的身体、一瞬间冷汗就冒出来。
他身上还有一些别的伤。
……淤青,叠加起来应该更痛吧。
“拳场、是什幺样子?”
酒精慢慢渗入伤口。
“反正…是你这种、千金大小姐看不得的地方。”他断断续续地说,竭力压抑呼吸,“倒是有些贵妇喜欢去……哈,上个月,还有人说要包我睡一晚。”
“诶。”我一怔,换一个新的棉球,重新按上去,“我朋友之前有说过…那种地方的男人,性欲都很强呢。”
“……操,忘了你也是贵妇。”
“我还是被你们强行抓来的敌人夫人呢。”
我忍住看见狰狞伤口的颤抖,将棉球细致的点按上去:“说到底就不该为强暴自己的人上药啊。”
“嘶、去找有栖修算账,别、别他妈赖在我头上。”
“疼得发抖就别弹舌说脏话呀。”
“谁他妈弹舌了,你胡扯什幺。”
“对不起,可能是我听错了呢。”
有栖真司:“……”
他疼得快没力气说话了。
即便如此、少年人面对曾有过亲密接触的女性,还是没办法躺平认怂,汗如雨下地来了一句:“疼得发抖也、嘶、也有力气肏你,等着吧、大小姐。”
门咔哒一声响了。
我顿了顿,把血水浸湿的棉球丢掉,和真司一起回头。
披着外套、显然刚从床上爬起来的成年男人表情微妙的看着我们。
有栖修:“……”
他弟:“……”
我:“……”
“……哥。”真司非常尴尬,“我那个…我回来了。”
“……怎幺受伤了?”
“回来的路上被跟了,甩掉的时候有人用刀划了一下。”
两边都打算当做没听见,非常默契地开始粉饰太平。
我。就。也假装没听见好了。
“据说已经叫了医生,具体可能还要有栖先生联系一下,我学的不是医学,最多只能处理到消毒了。……最好找医生来缝合,伤口很长。”
脚边的垃圾桶已经积蓄小堆鲜红棉球,有栖修只看一眼就明白怎幺回事,低低「嗯」了一声,拐出去给医生打电话,没过多久就重新走进来,站在身后盯着我处理伤口。
“谁干的?”
“不知道。”真司看我一眼,“肯定不是警方的人,但下手很黑,可能是黑道那边……我绕了好几条路,不知道他们怎幺发现的。”
“他们…确实该发现了。”有栖修平静地说,“这边不能再待,日程得提前了。你先养伤,真司,至于——”
他忽然低下头,盯着我望了几秒。
由于背对的姿势,看不清表情,只看见后方投射的阴影,发丝漫不经心垂落的弧度。
吸满了鲜血的酒精棉球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红色。
我尽可能平稳地扔掉了棉球。
“……大小姐,您想跟我们走吗?”他姑且问了一句。
——当然不想。
话虽如此。
“你们走之后…我会获救吗?”
有栖修笑了一声,“我不知道,这要看您的运气——说不定找上来的是警方的人。”
也说不定是那些穷凶极恶的黑道、是吧。
真司受了那幺重的伤才逃掉,这里被发现只是时间问题,况且他们不可能放任我联系家里,或许会直接把我丢在这里。
不带我走,就只能看运气,可如果真的跟他们走了……总不能指望他们半路好心把我扔给警察。
去向也是个问题。
“我的运气向来很不好。”
我丢掉最后一颗棉球,放下镊子,把手套摘掉,站起身问:“……为什幺?”
血液的猩甜、混着酒精与一次性手套的气味,弥漫在小小的房间。
有栖修比我高上不少。
垂着头望过来,视线刚好能对上。
稍微泛蓝的幽幽的眼睛,像狼一样,充斥某种兽类的特征。
“……或许、”
他擡手触碰我的脸,不顾一旁伤重弟弟的视线,强迫我张开嘴,舌尖缠绕上来。
……!
——究竟什幺人会在弟弟伤得满身是血的情况和抢来的女人接吻啊!!
肆无忌惮吻了半分钟,有栖修才低喘着放开手,半是自嘲地说,“或许…您确实运气不太好吧。”
倘若从未产生交集倒好。
可那样远远悬在天边的人——
倘若一时不慎、被他们陷在烂泥里的人遇上……
谁遇上了,会忍心放手?
哪怕亲手揉碎无暇新雪,污成一团烂在手心的泥水也好。
只要还躺在掌心,那都是他的东西。
在那之后不久,黑市医生终于到了。
我被塞在隔壁房间听着,医生夸了两句「处理得不错」,就相当熟练的上敷料包扎,没过多久就缝合好了——虽然真司并不想上麻药,但在有栖修的死亡逼迫下,还是不情不愿说了可以。
临走之前,有栖修亲自把她送到楼梯口,丝毫不在意我的存在、笑着说,“您最好别把那位小姐的事透露出去,医生,您知道规矩的。”
……我一点都不惊讶。
虽然那位医生竭力克制,但我清楚看见她临走前隔着门缝瞥来的视线了。
哪怕躲起来也没用,一时半刻是没办法掩盖掉某个女性存在的痕迹的,毕竟无论藏还是不藏,只要发现了就有可能上报。
大哥还有悟君他们,绝对已经找疯了,虽然这几天没机会看,但我确信网络上绝对到处都是找我的寻人启事。
……我的照片看起来应该都还可以,希望不要给公司股价带去不良影响。
中年的黑市医生沉沉地叹了一声,她应当比我清楚眼前这些人的身份,习惯了似的,半句话没多说:“我只是收钱办事。”
“您最好没收他们的钱,这东西谁都不缺。”有栖修很平静,“我无意冒犯,希望您不会对我们造成困扰。”
医生很快离开了。
“威胁刚刚救了亲弟命的人,”我抱膝坐在他的房间问,“真的好吗?”
“收钱办事而已。”
有栖修摘掉墨镜,简短地说,顿了片刻,转身翻出一件相当宽大的上衣递过来,“现在这件穿不了,换一件吧。”
……欸。
啊,对,我的衣服被真司的血弄得相当血案现场,经过这幺长时间、半湿地黏在身上,因为被体温渡热,我居然一直没发现。
我脱了衣服,刚打算接,又顿住了。
“但是、身上也都是血。”
湿淋淋的,在肌肤上划开鲜红艳丽的痕迹。
有栖修:“……那就去洗,夫人。”
男性倾身撑在床角,神色晦暗、声音比往常还要沉:“要不是真司还伤着…您又想被弄哭吗?”
从发现弟弟受伤,他的心情一直很糟,连向来带笑的唇角都变得冷淡,视线冰冷贪欲,衬得此刻威胁愈发危险。
“您非要引诱,我不介意被他听见。”
可我分明只是陈述事实。
他说成这样,我又没有受虐的爱好,只好抽几张纸姑且擦掉血痕,把衣服套上,自己去洗了澡。
真司已经睡了、不能打扰伤员,我回到房间,有栖修还坐在电脑桌前,不知道忙什幺,神情非常冷漠。
……还是不要打扰他了。
分明这样想了,湿着头发坐在床边翻先前拿到的书,一旁的男性却率先站起来走到身侧。
“?”
“别湿着头发坐在床上,”大概还是在意弟弟受伤的事,男性的语调仍很沉,“您生病了麻烦的是我。”
吹风机的声音响起来。
一边说那种等同威胁的话一边给抢来的女人吹头发,这个人到底怎幺回事……
而且,“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很在意。”
声音融进风声,稍微有些朦胧,但他还是听见了,“什幺事?”
“为什幺要用敬语?”
是什幺怪癖吗?羞辱别人的意味之类的。
……尽管有这幺想,事实应该并非如此。总感觉、他是认真的、无意识的在对我用敬词。
有栖修:“……”
湿发被手指撩起,自上而下细致地吹干。
吹风机嗡鸣的工作声中,人类的声线模糊不清。
我擡头看他。
发根传来细微被拉扯的感觉。
“……只是觉得、应该那样说。”
最终才后知后觉,听见他的回答。
*
*
*
*
虽然从有栖修的视角女主角是那种高不可攀的千金大小姐和有钱贵妇。
但,就、并不是啊!他的滤镜太重了!他潜意识里就觉得自己该仰望铃奈所以总是无意识做一些很……的事。
然而实际上,铃奈就是有点天然迟钝的正常(任性)女孩子而已,毕竟私生女这种身份也不算上得去台面。
有栖修的视角就…你们懂吧?他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