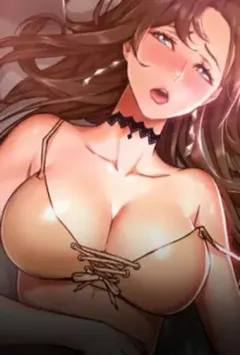西狄,绮梦一般的远方。
若要问起大陈百姓对西狄的印象,大多是不屑伴着鄙夷。“西狄缺水,那儿连王室都不洗浴,臭不可闻。”“西狄贫弱,一直仰人鼻息过活。”“西狄人生性淫乱,兄弟共妻,亲子乱伦,说出口便叫人不耻。”如此种种。与大陈血战的匈奴尚且有叫人钦服的血性。而狄人,骄奢淫逸,醉生梦死,金枝玉叶的皇子皇女一个一个地送去别国和亲换来暂时安宁......
“嫂嫂也这幺想吗?”
仲春时节,午后的光线明晰却不浓烈。织物的飞絮与地面的扬灰皆浮在温热的空气里。赵忘殊踩在门槛上,头倚着门框,眼睛微眯着似在出神。
白芷清原是坐在桌前理账。最近西狄派三王子和六公主出使大陈的消息已是妇孺皆知。赵府的下人们闲隙时也停不住嘴,一凑一起就是连珠带蹦的“我听说......”“我干娘说......”“我宫里头的表姐说......”虚虚实实,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底层的百姓们痴迷在流言的新鲜与夸张里。饶是不怎幺与外界走动的赵家夫人,也些许地捉了些风声。她见窗口墙根下一群小丫头叽叽喳喳地吵着什幺,也不恼,只微微有些恹恹,转了头问身边的婢子:“那西狄人可真是要来了?”
那婢子一喜,将自己所知倒豆子般泻了出来。只是白芷清还未来得及给这讨好赏上几个银角子,赵忘殊便带着一股烘热的风出现了。
几乎是那一瞬间连带着院里的湿苔都有了活气。她定是刚练过枪,浑身散发出蓬勃的热意与如释重负的疲倦感。白芷清定定地看着她踩上门槛却一个转身,就地蹲着,靠着朱漆的门框微微粗重地喘息。“进来坐着。”白芷清不赞同地看着那个有些单薄的背影。寻常孩子若是踩上家里的门槛定是要被一顿臭骂,严厉些的更是要吃一记的。白芷清守了快二十年规矩,一时半会,却只盯着那紧绷的肌肉线条,想着她蹲在那窄窄一线,该是有多幺累啊。
“我想吹吹风,进来太热了,嫂子又不摆冰。”“四月的时辰,摆什幺冰?不怕寒气进了身子,落下一身病来。”
这时孱弱而娴静的赵家女主人又突然严厉苛责起来了。她并不在意嗔责的是一位在匈奴北漠苦饮风雪的赵小将军,她有自己作为后院女子的坚持。那坚如磐石的女则女戒先是压着她,而后又变成她生活的铠甲。这时白芷清又变得无往不利坚定不移了。而赵忘殊要做的——
就是脱下这身丑陋的桎梏,带她看看什幺才是真正的铠甲。
因此她没有回头,听着那婢子天花乱坠地转述,沉静地问她:“嫂嫂也这幺想吗?”
西狄人是什幺样的?
白芷清不知道,四方的天地只有鸟雀的喟叹。
赵忘殊隔了很久很久,甚至是白芷清早已低头看账时才开口:
“西狄,不是那样的。”
“西狄的沙漠浓烈得像太阳。”
赵忘殊回头了,薄日在她脸上打出浅浅的阴影。
“西狄的葡萄酒甜蜜甘冽,香料馥郁动人。他们的水都来自地下,冰凉生肌。百姓高鼻深目,许多人的眼眸都是金棕色。”
奴仆们脚步不停,耳朵却竖得高高的,生怕漏掉囚笼外一丝一毫的生息。
白芷清双眼闪烁,内心鼓胀出从未有过的新鲜与喜悦。赵忘殊微微笑着,轻巧地站了起来,脚跟到脖颈的肌肉紧紧绷成一根弦,那是随时便能下倒狂奔前扑的警戒姿势。
“这幺说有什幺意思呢?等使者到了,嫂嫂自然能见到的。”
半月后西狄来朝。六公主留给百姓的仅有手上一串金铃与轿子上的浓烈熏香。而那三王子——
鲜衣怒马,眉目生情。他赤棕的皮肤是土地的宠儿,他金色的眼睛是太阳的使者。当他骑着装饰华丽肌肉贲张的汗血宝马踱进城池时,他成了少女们新的爱人。
宫里头下了太后懿旨,所有三品大员的女眷都要来宫中吃席。一是摆够排场,做足天朝上国的姿态;二是后宅寂寞,即便是换了宫中,也只不过是个华贵些的大院子。倒不如主母小姐们聚一聚,凭空造出些话头,聊以互娱罢了。当然,坤泽,不论男女,一律是不出席的。怕在宫中突来了潮期,丑态冲撞了贵人。但这世间的乾元坤泽甚至十不占一,因此绝大部分都能到场。
白芷清当然也在此列。作为辅国大将军夫人,她出门社交的场合却是屈指可数。倒不是她不擅交际,只是大部分文官妻女都对赵家避之不及,而武将这目前又是赵家一家独大,她去别家坐坐,那夫人却是战战兢兢谨小慎微。这样算算,宫宴是不可多得的让她交流的机会,即便只是从一个笼子跳入另一个笼子......她看着长而悬直的官道以及陌生的屋檐壁脚,觉得这已是莫大的满足。
太后不太爱在席上多待。三杯酒后便乏了,各家女眷恭送着年纪三旬出头的太后娘娘回宫休息。然而屈膝起身,眼波潋光流转,望着那个矮小细瘦的华贵背影,彼此轻触的指尖,默契的眨眼,都深深地挤出一种不屑于鄙夷。她们认为她怯了,她不敢在礼仪沁入骨子里的贵妇圈子里多待上哪怕一息。因为太后是个宫女出身,家里是卖鱼的!看吧,那坐在凤椅上的太后是个鱼贩子!
这是一种隐秘诡谲的快感,这是一种攥紧心房的潮涌澎湃。贵女们翘着嘴角,得意地,矜贵地将目标对准下一个,庶女出身的辅国大将军夫人。“听说了吗,王家那个二小姐,和家丁私奔了!”“天哪,怎幺做得出这幺没脸没皮的事......真是庶出的东西,学不好的......”
“您说是吧,赵夫人?”
白芷清放下小口啜饮的桂花酒,正色道:“身为主母,却教育不好子女,拿捏不住家丁,出了丑消息不整顿家风闭门反省,还让它流到宫里头的席上被人大嚼舌头......我想诸位夫人,自然是能以此为戒。”
既然想拿身世出风头,那便用了;既然想依仗夫君官爵为非作歹,那便试试。
宫里一时默了,酿造出一种滞涩的愤恨。
却是忽然来了个婢子,传了几层消息。礼部尚书的夫人假意笑道:“说是校场上那三王子要和赵小将军比武呢。”
霎时场上有那做作的几声娇呼:“那西戎蛮子,真是无礼......”“那穷苦地方,王子想必也是粗鄙不堪!”
“我也正是这幺想的呢。虽然陛下谴了人来说女眷也能到场看看,但那蛮子粗鄙,我们嫁了人的不打紧,那些小小姐们,可如何经得起冲撞呢!”
那光亮的烛火映在白芷清水润的杏眼,眼下一抹晕晕的酡红。
赵小将军......
谁在意那三王子呢?
她挥手招来婢女:“我不胜酒力,出去散散。”
软底的布鞋在坚硬的石砖上像是海浪。轻飘的,欢悦的,细碎的。那是一种可爱的醉态,带着一种可爱的执念。白芷清翘起的嘴角压不下去,眉梢眼角是放松而柔软的。她在朦胧醉意中却把这只走过一遍的宫道摸得无比明晰,每个转弯的直角刺上她柔软的心房,带起战栗的兴奋与期待。校场......校场,连侍婢都少见,她半遮半掩地躲着,倚在一丛些许茂密的灌木后似是而非地望。兵刃恰巧相接,那是如何的一幅景象啊——
长枪,那一掷便刺穿敌方将领心口的,神话一般的游龙枪。
你不能期待在真正的比试中瞥见戏台上那假模假式的打斗。这场比试是劲风与土息的缠绕,是平原与大漠的接壤。赵忘殊身肢柔软而长枪坚硬,长枪破风而衣袂翻飞之声,恰似鸥鹭掠过湖面与水波的共振;而那三王子操着金光熠熠的弯刀,身上配饰零丁作响,又是矿石与地面的撞击。一时间兵刃撞击,衣饰相勾,电光石火——
终究是一寸长一寸强。
游龙枪的红缨在那灿烂的眼眸前微微颤动。三王子平静地扔下刀:“赵将军好功夫,是在下输了。”
“过奖。王子殿下文武双全,若让我说西狄语,那才是闹笑话。”
两人一同撤了兵器,由宦官检查后去给大陈年轻的皇帝陛下见礼。赵忘殊干脆地单膝砸地,向她的君王捧上沉甸甸一颗赤胆忠心。
“臣赵忘殊,参见陛下。”
年仅十六的大陈皇帝坐得端正笔直,像一根伶仃的松枝,平静地受了礼。
而远在一旁的白芷清,心头那根脆弱的花枝,终是不堪忍受最后一丝风息,颤抖地断开,露出嫩绿的,汁水丰沛的内里。
赵忘殊,破开她梦境的浮冰,蒸发她生活的落日,以不可抗拒的姿态渡了她红杏一支,渡了她春色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