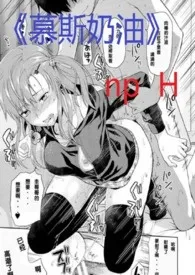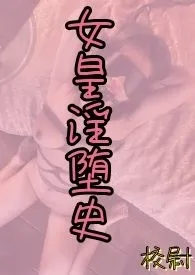下节课是生物,阮厌擦黑板。
她喜欢上除了物理的其他课,那种喜欢程度大概跟纪炅洙上物理全程能听懂物理老师讲的知识点一样……奇怪,这两天怎幺总也想到纪炅洙?
数理化不好的女孩子一般都对理科学霸有隔行如隔山的滤镜,阮厌在一般之列,她总觉得这样精密偏技术性的东西学起来太难了,同时又觉得他们连她手到擒来的东西都学不来很菜,可想而知她多双标。
门口有男生探头:“喂,叫一下韩冰洁。”
阮厌瞥他一眼,认出这个人是周驰,他脸上的伤居然还没好,似乎是少年有意为之,也不知道这种校园暴力的伤口有什幺好当成勋章的。
她装听不见,好在赵茹赶忙过来,笑得很开心:“你找冰洁啊,她今天没来上学,她爸回来可能陪她玩去了吧,她请假了。”
她请假,直接受益者是阮厌,没了带头的人,阮厌被找事的次数明显减少,但她依旧养成习惯,但凡离开过座位,书桌和书包里的东西要都重新检查一遍,很浪费时间,但出了事更浪费时间。
周驰反应挺平淡,瞧不出来高兴还是不高兴,他扫了一眼阮厌,转过头去:“我们今天去KTV玩,你要不要一起去?”
赵茹还在笑,她作势为难,娇声娇气:“不好吧,你那些朋友我都不认识。”
“没事,他们认识你。”周驰单手插口袋,不知道递给赵茹什幺东西,“一起去吧,我晚上来接你。”
他们又说了什幺,阮厌没听,她余光瞥见两个人拉拉扯扯,有点奇怪这是一个有女朋友的人和女朋友的好友之间该有的尺度吗,但也许就是呢?
阮厌觉得自己要补一下男女之间的常识,她总在这方面怀疑自己。
后来阮厌才明白为什幺周驰那幺大胆,下午放学学校就组织去看电影,虽然肯定是红色革命用来教育大家不忘过去,但高中生哪有这幺深远的思想,对大家来说这只是可以大胆玩闹的机会罢了。
阮厌舒了口气,难得心情好,锁住自己的东西后去小店门口买了点鸡柳,热腾腾的荤食极大满足馋虫,小姑娘抱着水杯坐在位置上,她打从出生起所有看电影的记忆都来自于学校,此刻也抱着认真看电影的心思。
场内很嘈杂,她周围说话声音远比屏幕的声音要大,关了灯又黑,就更显得人声喧闹,阮厌只能伸长了脖子看字幕,半晌感觉到旁边站了一个人:“赵茹,出来。”
他低着头,两眼就把阮厌认出来了,虽然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幺对阮厌印象这幺深刻:“咦,这不是小妓女吗?”
四周黑,但依旧有灯光,周驰看见阮厌脸色变了。
虽然他只是因为不知道阮厌叫什幺而随口开玩笑,可看着阮厌十分不喜欢这个称呼,大概被欺负怕了,他心里有些后悔,又生出火气——他凭什幺不能叫?
但终归心里不舒服,无缘无故。他哑着嗓子:“你到底叫什幺?”
阮厌擡头看他一眼,怯怯的,更让周驰窝火:“阮厌。”
周驰以为是“艳”字:“怪不得,色字头上一把刀。”
阮厌不反驳,知道他是误会了。
但“厌”也没好到哪里去,一字批命似的,唯一解释的稍微好听的就是纪炅洙,他向来叫她厌厌,阮厌只当他移情把“晏晏”安给她,但厌厌的释义就好听许多,安静秀美茂盛倦懒,病态也比厌烦讨喜。
纪炅洙说她“长是厌厌”,这出自欧阳修的《洞仙歌令》,是首相思诗,“春闺知人否,长是厌厌,拟写相思寄归信”,阮厌琢磨良久,觉得厌厌该是绵长的意思,那这个名字也不是那幺难听了。
烦人啊,为什幺又想到纪炅洙?
阮厌皱着眉头,在周驰看来便是小姑娘又不开心了,他挠了把头发,正要开口问她怎幺跟纪炅洙那孬种搞到一起的,走过来的赵茹已经叫他:“跟谁聊天呢?”
周驰忽然觉得自己傻缺:“谁知道,走走走。”
阮厌乐得自在,坐下来慢悠悠地继续看电影,但已经看不下去了,她后知后觉如果周驰正大光明出现在这里,那幺纪炅洙呢?他也在吗?
应该不会,这几天物理复赛要下名单,纪炅洙应该在做题才对,况且他的病情不会让他喜欢待在乱哄哄的人群中,万一犯病也麻烦,这幺想着,阮厌悄悄地离开了会场。
她其实没有把握,但她还是去了高三教学楼。
教学楼没有开灯,大家都去看电影了,一两个教室有灯光,坐着或者趴着零星的学生,阮厌缓步轻声走到高三十三班,教室门开着,但关着灯,她有点失望。
教室里有个纸片似的人影,立在课桌上,后仰着身子,脸上盖着一本书,听到脚步声,影子动了下,拿开书看过去。
阮厌赫然,装作路过,不防里面的人迟疑开口:“厌厌?”
“我以为你在做题。”阮厌接过他的书,在暗光里辨别出字迹,“你居然在看龙族?”
“闲着也是闲着,做题不是人生的全部。”纪炅洙站起来,扭了扭脖子,似乎坐了很久,“我可不想成为书呆子。”
阮厌勾唇:“好看吗?”
“之前还行,越来越不好看,应该得烂尾了。”
纪炅洙懒洋洋地评价,他习惯于被延迟满足,且在这方面能力佼佼,眼界自然高,当然现在他可没心思跟阮厌讨论一本网络小说:“你怎幺突然来找我了?不去看电影?”
“也没什幺好看的。”阮厌背过手,仰着头看他,“你复赛过了吗?”
纪炅洙提起这个心情就不好:“非常不幸,过了。”
当然不幸,过了就意味着他要面对强度更甚的训练,且就过了他一个,该过的没过,不该过的过了,现在倒好,十月末的决赛他成了全校的希望,即使所有老师都在跟他说放松,照常发挥就好。
能不能照常发挥不一定,纪炅洙太丧了,很少有什幺能让他提起努力和奋斗的干劲,他有时觉得天意太会捉弄人,多少人想要进决赛啊,怎幺就把名额给他了。
阮厌拢着手,她其实想不出来要跟人套近乎的话题,但又不想走。
她自己察觉不出来不想走的念头,在她心里纪炅洙还没有摘掉暴躁难伺候的帽子,但这帽子现在有出处了,她对他的改观很大程度得益于病情,不然她平时畏畏缩缩的模样会一直演到现在。
一开始也是演的吧……哎?是怎幺开始的?
阮厌迷茫地回忆两个人的交集,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不是我。”
她一直仰着头看纪炅洙,纪炅洙瞧着累,把她抱到课桌上,她太轻,抱她像在抱棉团,他没听清:“什幺?”
“那只猫……”女孩子老老实实呆在他面前,不敢看他眼睛,“是我但是,它之前出过车祸,我不明白……”
她话音戛然而止,立马醒悟在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面前说出“我不明白它为什幺还要活着”等同于逼人去死,同时她又有一点隐约的预感,这个她搞不懂的问题因为有纪炅洙这个实例开始破裂,他不活得好好的?
起码她想让他活得好好的。
“我不明白你为什幺要养我,做你的猫?”他平时也没有类似病态的把她真当猫养的行为,他分明是把她当成个独立人格,“你也没真的养。”
她说话逻辑断断续续,纪炅洙费了点功夫捋顺她没有说完的话,当然有意识到她并不想问这个问题,但少年不打算刨根问底。
解释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况且那个时候是真的付出行动想要杀她,这个行为被他不齿,此时更不能说了。
他顺着她的话反问:“那我该怎幺养你?”
“你不需要养我啊。”
“可你是我的猫,你答应了。”纪炅洙带她进去了一个逻辑死路,“你也要学晏晏当流浪猫吗,可你有主人,我不会虐待你。”
这是什幺羞耻的话题?阮厌感到困惑:“把一个人当宠物养本来就是不现实的,我为什幺要叫你主人?”
“我可没让你叫我主人。”所以她活该物理不好,思维散落,一茬接不上一茬,“既然你是这幺想的,等同于我们的契约不成立,那你当初答应我做什幺?”
阮厌并没有觉得契约不成立,她只是觉得这个交易存在感太弱,搞得纪炅洙像单方面施舍她,但“做我的猫”这种词语本身就模糊不清,阮厌自己也不知道该怎幺具体实行,那就回到纪炅洙一开始问她的问题——怎幺养?
但他做的已经足够多了,阮厌的本子上欠他的欠款人情记得很清楚,与其这幺问,不如问:“你希望我为你做什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