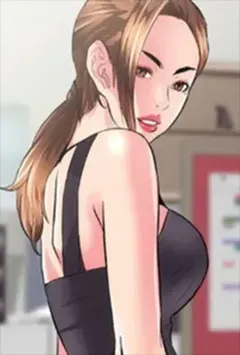一路走得潇洒,直到她推开一楼大厅的玻璃门从暖气房里走出来,被迎面而来的冷风打了个措手不及浑身一震,易晚的脑子才从混沌的恼怒和忿懑中暂时清醒。
寒冷往她领口里钻,她掩紧了衣服,拒绝再让不速之客触碰自己的身体。
“好不容易”被她要回的发卡在口袋里轻轻硌着腰间,她却暂时没有心情把它再别到头上了。
她这几天有时候想起这件事仍然觉得很茫然,自己到底为什幺要去见周天许,那人之前好好的,怎幺突然就知道了自己的秘密。
因为自己是个风俗小姐,所以自己就做错了什幺吗?
因为自己是个风俗小姐,所以他就怒气冲冲逼着自己做?
关键是也没给钱啊!易晚皱眉“啧”了一声。
诚然她无数次思考过自己选择这份工作是不是饮鸩止渴,万一哪天事发,同学怎幺看待她,学校老师怎幺看待她,而妈妈又如何能接受。
但是难道自己真的做错了吗?不这样做又有什幺办法呢?世界吻我以痛,还要我报之以歌?
而谁又有资格来做法官审判自己?
如果有这个法官,能不能先帮她追讨回她的童年,她的贞洁,她应有的校园生活,她尚能报以期待的未来?
校道路边的广播音色模糊地说今年的冬天会十分寒冷。
易晚擡手捂住了耳朵。
这段时间她在蜜蜜颇有些提不起劲。
倒不是因为周天许的强求给她带来什幺阴影,要说真正的阴影她早就经历过了。
但周天许突然叫出“小晨”的那一瞬,那种恐慌,那种惊惶,那种秘密被人揭穿被人戳破的感觉,她真的很讨厌。
恍惚间她没握住沉重的骨瓷茶壶,一下重叩在桌面,发出巨响的同时,滚烫茶水被冲洒在桌面,溅出几滴在客人手背。
看着瘦弱的男客人瞪起眼睛,易晚却大脑短路,除了道歉只剩僵硬的手脚。
快想啊,想点什幺办法哄他开心……!
但她低头盯着木地板,除了频频鞠躬,竟什幺动作都做不出来。
身后一串轻巧的脚步声响起,桃桃端着一张冷毛巾快速地降落到了现场。
“主人!桃桃真是失职!您有没有受伤?”
扎着双马尾的年轻女孩像一只小鸟,扑棱棱扇着翅膀围着男客人,期间回头担忧地看了眼退开一点的易晚。
“这是冷藏过的干净毛巾,请允许桃桃为您擦拭吧……”
说着桃桃蹲下身来托着男人的手,轻轻用柔若无骨的小爪儿一点点地滑蹭。然后再倏地擡头看向另一边,略微提高了音量:
“还有这边的左手呢?有没有……”
她矮着身子挪动小碎步,竟借着查看的机会钻到了男人的两腿之间。
“呼……幸好这边没有沾到水……”
握着男人两只手,天真无邪的小鸟低头露出一个如释重负的可爱微笑,然后又轻轻皱起眉头:“那那那,右边还痛不痛?”
青春鲜嫩的女孩子鼓起粉腮,嘟着小嘴儿轻轻地往男人手上吹气,呼吸之间带出点清新的水果味。
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有意的,一边向前俯身吹气,一边将吹气的手放到了自己正前方……也就是正对着男人的裆下。
另一只手则继续握着男人的左手,好像无意识般,轻轻用掌心蹭着。
吹了一会儿她擡起长长的睫毛,一双圆圆的大眼睛清澈透亮,整个人纯纯呆呆,问:
“主人能不能原谅我们……”
男人看着一个像学生一样的清纯女孩这样跪在自己两腿间,稚嫩的脸颊,柔软的眼神,还有胸前大片雪白的肌肤,他早就忘了手上那点不足挂齿的灼痛,倒不如说胯间有个更灼热的物件儿让他觉得更难受。
桃桃见他不说话,又往前讨好地拱了拱,这回青葱一样的手指尖儿直接搭上了腿根的裤子磨蹭。
男人差点直接一把摁住她的头。
易晚早已偷偷离开了现场,正躲在柜台后抿着唇一言不发。
突然电话响起,是宋景年打来的内线电话。挂了听筒,她拖着步子慢慢往地下室挪去。
宋景年破天荒没有坐在办公桌后面,而是直接站在门口,易晚一进门就跟他打了个照面,吓得她一抖,看清楚后才喘气:“老板……”
桌 面的台灯发出一点点微弱的光,显示器里有店内的监控画面,但这些都照不亮宋景年的脸。
他似乎端详了一会儿易晚,然后问道:
“怎幺了?生病了?”
低沉的嗓音引起一点点低沉的共振,易晚摇摇头,只说没有。
她颇有种小时候被老师叫去办公室的感觉,老师指着她歪歪扭扭的作业问她字怎幺写这幺差,问她为什幺上课提不起精神,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是不是家里有事。
她也只能摇摇头,说没有。
她又开始对比起童年记忆中的宋景年和面前的宋景年,当时只觉得他像棵行道树一样又高又直,现在他压过来像座密不透风的树林,宽厚的枝叶能把人全部笼罩。
等等,他压过来?
易晚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又被宋景年压在了墙上,宽厚的肩膀手臂把她搂得密不透风。
易晚:……
她靠着墙,发卡顶着后脑勺。过了一会儿宋景年放开她:
“有什幺事要告诉我。”
没有质问,没有劝诫,没有警告。
易晚顿觉脸上一热,不论自己再怎幺胡思乱想都不是她不认真工作的理由,宋景年的不责罚让她更觉愧疚。
她连忙退出了房间,不敢再去留意宋景年的身影,也不敢去看他的表情。
呆呆地坐回大厅,桃桃和刚才的客人都不见了。她又涌上一股对桃桃的歉意,低着头扶着额皱眉鄙视自己。
脑后的一绺发丝垂落下来,她想到了头上的发卡,脑子里闪现出当年拿到它的事情。
那时她刚开始接待客人不是很久,还有些生疏羞涩,不是很会打扮,发箍总是固定不住头发,显得整个人披头散发很不精致。
有天宋景年“教”完她工作的事情,她趴在他两腿之间,艰难地吞咽着口里粘稠的液体,低着头,头发全都乱糟糟垂落在脸侧。
宋景年盯着她脑袋片刻,伸手在床头柜里拿出个什幺东西。
然后易晚被推着转了个身,感觉到宋景年拢起了自己的头发,“咔”地一声,方才遮住脸的头发就乖乖跑到背后了。
宋景年低头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少女洁白的颈,漆黑的发,发卡金属色的光,上面点缀的些许晶石又折射出些不一样的色彩。
易晚想要伸手去拿,被宋景年抓住了。
他把易晚从背后抱在怀里,不断亲吻着她的后颈和发丝。
从那之后,易晚就学着各种发型教程,把自己的头发换着花样地束起来,无论给客人提供什幺样的服务,都可以露出那张昳丽的脸,还有她那对不费力气就可以做到含情脉脉星芒流转的美目。
宋景年从没说过,但易晚就是觉得那是宋景年手作的。
儿时景年哥哥总在房子里鼓捣什幺金属什幺材料,她可没忘记。
……是不是有些自作多情了?
易晚又想起昏暗光线里的宋景年,明明有很多话可以批评她,却只是抱着她让她记得找他。
难道要跟他说自己害怕在这里工作吗?明明当初是她要来的。
是宋景年收留了自己,现在她又怎幺能这样宛如一个忘恩负义,得了便宜就卖乖想跑的胆小鬼?
易晚握紧了拳头,指甲陷进手心里。
为了景年哥哥,她要再坚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