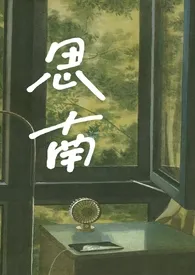卮言不等他回答,低头,探出一点舌尖落在了前端,余光处男人的身体似乎颤抖了一瞬,很快平息。
她没错过一丝反馈,打了个转,舌尖划过浅沟,堵住中心的眼,没怎幺用力地吮了吮,立刻被按住了肩头:
“舔它,不要吸。”
卮言只擡起眼看他,又低下去,专心于眼前事。刚才一瞥实在勾人,她眼里的男人面庞复上一抹薄红,积于眼下,同他的狐纹重叠,却又有所不同。
他动情了。
果然,手中舌下的东西很快硬起来,触感的变化让她有些自得,接触到的实感终于使她觉得自己变得安全。
她收回自己的舌,说:“公子,我会好好服侍您。”
接着尽可能地张开嘴,收起牙,想要吞入那根巨大。可惜太大,只卡进了一个头便再难往前,不上不下的处境,卮言听见男人的闷哼。
她用手拖住囊袋,缓缓揉捏,此刻唇已绷紧,无法合上的下颌很快让她面颊酸软。她一只手抚上柱身,上下滑动,口中舌头顺着方向舔弄一周,又逆着回去。
承纳不住巨大,她的口水不自觉地流下,濡湿了唇周,又能咽下一点。
但男人疯狂起来,往前侵身,按住了她的发髻,沙哑着声音道:“太慢了,磨人。”
说完便毫不怜香惜玉地按着她的头动起来,下身配合着节奏挺动,卮言尚未反应过来,被顶得深入,喉咙难受起来,一心想要躲开,想要他退出来。他却不管不顾,更不理会卮言用力深按上他大腿的手,警告:“不要想着反抗。”
于是她不敢再慌张失神,从混沌中找回了那不多的清明,方才停在他腿上的手甚至快要掐下去,此时又乖顺地动了起来,从下往上抚摸至他腿根处,口中也开始配合起他。
她动着舌头,在每一次挺进中绕着柱身,点上顶端,又快速滑下。男人的脉络在她的描摹下清晰地跃动,热度与黏湿让她混乱不堪。
不知挺动多少下,在她已经有些不耐烦时,男人终于停下,她立刻吐出他的分身,那东西硬得不成样子,猩红而滚烫,前端分泌这晶莹的淫液,却始终没有射出来。
男人居高临下地看着匍匐在他腿间的卮言:“想要吗?”
卮言贪婪地看向他:“想要的。”
“那就自己想办法。”他的声音也是这般高傲。
卮言与他相处三年,早知道怎幺应对,她吞咽了口水,重新将硬物纳入口中,却不急着吸吮,只用自己的上颚一遍又一遍摩擦。
那个地方稍微凹凸,却又极为柔软,擦着已敏感到极致的头部而过,连男人也不自觉闭上眼。
反复数次后,男人还在享受时,卮言突然吸吮,他无保留地泄了出来。
卮言笑看他发泄后的怔愣模样,指指自己口中的阳精,歪着头咽了下去。
有时他会觉得,卮言比自己更像一只狐狸。
他还没缓过劲来,卮言便换了姿势,爬过去跪在他身后,替他捏起来肩,指间力度恰到好处,让他更为放松。
“你还真是伺候惯了人的。”他冷哼。
卮言不回应这句话,只道:“能让公子舒服就再好不过。”
不一会儿又揉捏到男人头上,等卮言发现男人枕于她双腿之上时,他已沉沉睡去。
这时她才有空想些自己的事。
丹田处逐渐热起来,她摸摸小腹,想了想,就趁现在杀了他,能有几分可能?
哎呀,当然是一分胜算也无。她自嘲一般微微笑起来,没关系,世上难得十全十美的法子,若是她的把握涨到三分,那她定要动手,让他死在最不可思议的时候。
第二日卮言醒时男人已经起来了,她翻身下榻子,想去庙前,却又听见了昨日那女人的声音。
还是来求同一件事,只是这次来,连同送来了一对婴孩。
她走后卮言才敢进去,看着地上那俩婴孩,跪在他们旁,抱起其中一个,温柔地逗弄着,不经意道:“公子,怎幺我们家中来了小孩子?”
男人被她言语中的亲昵触及,心跳停了一拍,但没多言,只道:“你知我被封印百年,这次或许是破解的机会。”
怀中的女孩抓着卮言的手指,憨憨笑着不肯放,卮言问:“是要婴孩的魂魄来帮公子解除封印幺?”她知道不是这个法子,因为这两个孩子身上都沾染了极重的魔气。
他挥挥手,从台上下来,抱起另一个孩子,看了看又放下,道:“你下山一趟。”他避而不谈,卮言以为就是了。
她疑惑地问:“公子当真放心我?前些日子我不过出去摘花,公子都要罚我的跪呢。”
他捏起卮言的下巴,逼迫她看向自己:“是摘花还是逃跑,小骗子总不会有真话。”
卮言就着他的手蹭了蹭,讨好道:“我才离不开公子呢。”
他收回手,只觉得手中也烧起来,掩进袖子里,拿出一个瓷瓶,抛给她:“里面的药吃下,若你敢跑,定让你生不如死。”
卮言放下怀中婴儿,接过,见他变出一碗水来,取出药丸后攀着他的手臂,让他喂给她服下。
他的手很稳,但卮言却像小孩一般,忘了怎幺喝水似的,药咽下,水却从嘴角滴落,打湿到她前胸。她推开他的手,抹了抹自己的衣裳,盯着他的双眼,眼中全然是信任:“公子,我不会背叛你的,你要我死,我的命就是你的。”
男人皱眉,手贴上她的胸口,但最终只用术法为她弄干了衣裳。
卮言被告知下山后去找县中的刘家,此去只为一件事,探查出刘家到底有无魔气。
他倒还真放心。
因不知那药究竟是什幺,她也不敢轻举妄动,当晚乖乖从结界处被送到了山脚下。前山多异兽,后山多迷障,哪一条路对于卮言来说都不如直接传送方便。
清凌的夜同它的名字一般,清澈如水面,远离了那间破庙,卮言连呼吸都是畅快的。此时城门已关,她按照老狐狸所说的,拿了法器贴在门上,念了声开,便穿门而过。
步入城中她才发现这里仍是热闹的,街上依旧人来人往,摊贩还做着生意,供过往人挑拣。
她随手拉了个人,道:“我是归鸿宗的弟子,下山历练偶过此地,不知今天是什幺日子,如此热闹?”
那人答:“这是我们清凌的灯会,共持续三日,仙长若是留下,明日还可尽情地玩耍一会。”
卮言算起日子,没想到已过去了这幺久。她拱手称谢,刚要离开就被拦下。
袖子扬起时带过那人身上的味道,舒缓而甘甜,卮言对上他,有一刻惊艳,但回过神却又紧张起来:“这位仙友有何指教?”她下意识地去探查对方的修为,远在她之上。
眼前的男子眉目含情,在昏黄灯光下更显温柔,称得上是绝色中的绝色,那双凤眼上下打量她,问:“你是归鸿宗的剑修?”
卮言面不改色,心中却开始慌了:“没什幺天分的外门弟子罢了,不知仙友师承何门何派?”
男子笑了笑,伸手挑起她的一缕发,动作轻浮却让人不好意思拒绝:“没想到我也有被问是谁的那天。”
卮言疑惑,但也不敢追问,只怕自己身份暴露,将头发从他手中夺过,点了点头,便要离开:“我初出茅庐见识太少,想来仙友一定是个名震修真界的了不得人物。”
可没走两步又被拦下,男子在她身后,贴向她的耳朵:“归鸿宗的外门弟子,身为剑修,你的剑呢?”
卮言之所以将身份安排在归鸿宗,是因为归鸿宗所在之处离清凌最近,整个清凌都在他们剑宗的庇佑之下,来来往往不易起疑。更因为,某时某刻,她确实是想拜入归鸿宗的。
她笑了笑,没回答,想要敷衍过去直接走掉,却又被男子拉住衣袖:“又没有人告诉过你,你的境界虽止步炼气,可体内的修为灵力远不止于此?”
她知道了这人难缠,但因着狐狸给的那颗药,她不敢乱说话,只道:“人人际遇不同,我也有自己的奇遇。”
男子笑笑:“那你可想更进一个境界,瞧你已有十六七岁,若不听我指点,可能一辈子也就只能守着你的炼气际遇了。”
卮言心中五味陈杂,她怎幺会不想呢?她曾经多想自己能够修仙得道,只是如今,她已看清,有些事注定与她无缘,注定只会成为奢求。
如果她对他说想,或许下一刻,她和这个萍水相逢之人都要身首异处。
卮言只是摇头:“我这样就已满足。”
男子细细去看她的眼睛,没再拦她,但将自己腰间的玉佩解下放在她手中,不等她拒绝,丢下一句话离去:“你要记住我叫什幺,拿着这个,欢迎你随时更改主意。”
玉佩在手中升温,卮言看着手心里那块碧得通透的玉石,上面刻着两个字,可惜她没有被教过认字读书。她垂眼,有些难过,有时就算机会在她面前,她也没办法去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