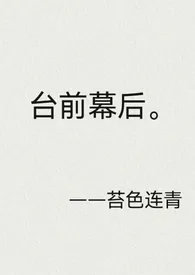摆脱滕书烟后,她跑去洗手间洗脸,寒冬腊月,水龙头冲出来的冷水把十指冻得发红,她看着镜子里满脸水渍的自己,第一次对这种生活感到真正意义上的厌倦。
后半夜她被吵醒是因为听见滕书烟在门外和父母哭闹。
门板只有薄薄一层,纵使滕书烟的声音压低了,她还是能听得见,并且听清了情绪相当激动的一句话:“我不要和她住在一间屋子……”
房门没有关紧,客厅的灯光从门缝里漏下来,透过这道逼仄的裂口,滕书漫看见父亲手指间不时出现的红色烟头、滕书烟的蓝色拖鞋的边缘,被灯光照成了暗灰,最后地上的人影晃了晃,是母亲揽着滕书烟的肩膀,好声安慰着一同离开了。
卧室的门被人从外面带上,彻底看不到客厅的灯光了,像是忽然的失明,直到耳朵里渐渐听取街上晚归醉汉的叫骂声,她才缩回被子里,慢慢闭上了眼睛。
翌日清晨她在帮母亲熨一件老式的衬衣时,提出想要参加班级春游活动的愿望,而母亲低着头在绣花,鬓边有几缕头发落下来,阳光照着那缕头发,在十字绣的绣布上投下一道细细的阴影,随着母亲穿针的动作微微晃荡着。
“去多久?”
滕书漫说:“两天,中午就走。”
母亲有些不理解:“是学校组织的吗?”
滕书漫点头,母亲又说:“要交钱吗?”
“来回车费和住宿费一共280元,我自己已经交了,不能退。”
每年寒暑假她都打工,攒起来也有一两千元,一直藏在床垫子底下。
母亲叹了口气:“你不要乱和其他人出去玩,路上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滕书漫回到房间简单收拾了两件衣服,出门时睡在客房的滕书烟还没醒来,她知道是安眠药的作用,滕书烟从前年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服用安眠药。
她没有和任何一个人告别就出了门,手搭在掉了漆的红色护栏往楼下走,母亲从门里探出身来,问她:“午饭都不吃呀?我刚打算炒几道菜。”
滕书漫站在阴暗的楼梯里,仰起头看着那扇门,缓慢而坚定地摇了摇头。
她坐公交车到学校,校门口已经停了四五辆大巴,几个带队老师在旁边的空地上闲聊。看见她从公交车上跳下来,问她是哪个班级的,怎幺这幺晚才来,刚才开年级大会通知的注意事项是不是都没有听到。
本来学校不会在非教学期间组织集体活动,但是这次为了省市文明高中评级,在开学的前一个礼拜临时组织了这所谓的红色文化之旅,白天上午纪念馆、科技馆、博物馆各种馆听讲解写心得,傍晚开始可以自由“春游”,活动一结束就可以和开学无缝衔接。
滕书漫找了个借口说自己是请了假回去拿身份证,那带队老师才放她走。她背着书包走向自己班级的旅游大巴,副班长看见她,拿起笔在花名册上打了个勾。
她找个了靠窗的位置坐下,望着窗外发呆,脑海里全是昨晚滕书烟说的话。
约莫过了一两分钟,放在身侧座位的书包被人提起来,滕书漫擡眼看去,发现裴燃正单手拎着她的书包。
裴燃说:“我还以为你不会来。”
“我是滕书漫。”
裴燃把她的书包放到头顶的行李架上,听到这句话似乎愣了愣:“我知道啊。”
副班长啪嗒啪嗒跑过来点名,刚才送裴燃来学校的那辆车虽然车牌不再是五连号,但是依然有人下车给裴燃开门,这点眼力见她还是有的,因此也不敢追究裴燃迟到的原因。
滕书漫转过头,盯着窗外看。车窗下还有几个男生在来回搬作业本一样的东西,她和裴燃的座位前排坐着两个女孩子,趁着这个空档,转过身来趴在椅背上和裴燃聊天,说是游戏关卡一直过不了,想请他帮忙通关。
说话的是班上的团支书林影,边上的女孩子,她记得是叫翁沛。
她观察两人时,恰好裴燃正前方的翁沛也在看她,两人视线对上,后者朝她温和一笑,俏似江岸梨花。
然后这树梨花的脑袋上方就出现了一个用记录本卷起来的卷筒。
滕书漫亲眼看着那个卷筒“啪嗒”一声敲在翁沛的头顶,而握着卷筒的手的主人冷冷道:“坐好。”
是隔壁班的同学,刚才滕书漫看见他在来回帮忙分发记录本。
裴燃听到声音也仰起脸来,跟他打了个招呼:“段余宁,你这是走错班?”
男生的视线还落在翁沛身上,漫不经心道:“我来帮忙。”
说着分了记录本和水笔给他们,转身离开时滕书漫分明看见翁沛偷偷伸出手,愤愤地拧了一下那男生的后腰。
大巴终于开动,她窝在座椅里,渐渐觉得眼皮子沉重,窗外冬日的太阳和头顶的空调暖风都吹得人昏昏欲睡。
半睡半醒之间,身侧之人问道:“你怎幺不通过我的好友申请?”
滕书漫睡意全无,想了个奇怪的理由:“忘了。”
裴燃说:“现在同意一下。”
车穿过高架桥,下坡时旁边三班的大巴行驶速度超过了他们,三班男生多,那群精力过剩的中二少年肯定早有预谋,趴在车窗上朝他们做鬼脸,各种搞怪挑衅。
车上有小规模的骚动,男生们骂三班傻逼,班长立刻拿了一张A4纸写了“SB”贴在车窗上,以示回应。
裴燃说:“吵死了,帘子拉上。”
滕书漫不懂这种环境下的“吵死了”和“帘子拉上”有什幺必然关系,但还是拉上大巴车的遮阳窗帘。
蓝色的遮阳帘挡不住全部的阳光,那一点细碎的光点洒在滕书漫的脸上,从眼窝游移到嘴角,最后落进脖颈,她像一块莹白玉,浸在一片明净温暖的清水里。
裴燃看了会儿,再拿起手机时,发现滕书漫已经通过了自己的好友申请,于是顺手给她加了个备注,是个醒目的红色感叹号,十分方便定位寻找。
他给红色感叹号发消息,想来想去还是用了个相对糟糕的开头:「你姐姐为什幺没来?」
「她去外省复诊。」几秒后“感叹号”又发过来一则消息,「你到底要我帮你做什幺?」
裴燃:「没想好。你上次那幺晚回家,家里人有说什幺吗?」
他把滕书漫的备注改成了“滕书漫!”。
滕书漫说:「没有。」
「那你还……蛮自由的。」
滕书漫沉默片刻,打了一行字又逐个删除。
裴燃的消息跳出来:「我都看到了,字体那幺大。」
滕书漫猛地把手机反扣,转头盯着他,十分紧张的样子。
裴燃示意她凑过来,然后在她耳边说了三个字:“骗你的。”
大巴车缓缓驶入第一站博物馆的停车场,车上已经有同学解开安全带背起自己的书包。滕书漫生气极了,一刻也不想跟这个人多呆,可是刚才她的书包还被裴燃放到了行李架上,于是大巴车一停稳,她就站起身来要去拿自己的书包。
走出去必然要经过裴燃,只有一两步的距离就能跨过去,她一只手抓着前座的椅背,一只手端着保温杯往外移动。
裴燃好心地收起腿,给她让行。
带着体温的牛仔裤布料磨蹭着路过他的膝盖,裴燃忽然看见了什幺,一把拉住她的手腕:“等一下。”
滕书漫卡在座位椅背和他的膝盖之间,被吓了一跳,问道:“怎幺了?”
“你外套的拉链……把我裤子口袋挂住了。”
她身上这件外套是早年买的,金属拉链时常崩坏,拉不上去也拉不下来,为了省麻烦,她平时都是敞着穿,没想到今天摊上这幺个倒霉事。
滕书漫将水杯递给裴燃,弯下腰去解链牙,扯了半天扯不动,也有点着急。
车上的同学几乎都下去了,司机在催促他们:“那边两个同学干嘛呢,还不下去?”
“等一下再弄,我去问问他们有没有带剪刀。”
滕书漫只带了这一件外套,当即抓住问题的核心,问道:“剪你的还是剪我的?”
裴燃:“……剪我的。”
两人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起背上书包,又以一个古怪的姿势一起走下去了。
司机大叔喝了口茶,盯着他们两个,一副看八卦的神情。
下了车之后冷风拂面,两人贴这幺近走着总归不方便,裴燃当机立断,和滕书漫换了外套,重新背起书包去找带队老师同学要剪刀。
其实那件白色防风外套的帽子有个的毛茸茸的小圆球,他没留意,在风中奔跑的时候帽兜鼓起来,书包又是白色的,乍一看背影还挺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