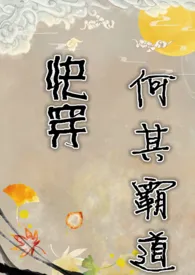阮靖面色尴尬,他擡头看见如意公主抚着肚子,怒急攻心地看着他,像是在等一个解释,萧侍卫长虚虚扶着如意公主防她晕倒,一双眼也是冷得像结霜。
他手足无措地低着头,扶着地就要摇摇晃晃站起身来,却发现胸前衣衫大敞,更觉尴尬地滑坐在地上,只是皱了眉盯着如意公主,讷声道:“我、我也不想这样的......”
锦娘从碎片里慢慢坐起来,懒懒地用手支着地,斜眼看了眼阮靖,嗤笑了一声,又扬面对着如意公主缓缓道:“公主,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你府上的干儿子,父母究竟是谁吗。”她说半句话就喘上一喘,皮肉里嵌进去的瓷片令她疼痛难耐,说上一句话已是十分吃力,因着心底喷薄的恨意,忍着疼非要说出令人不痛快的话来。
阮靖恨声喝道:“住口!”
如意公主反身抽出萧行之腰侧的配剑,刷的一声长剑出鞘,她扬身将剑口对着阮靖胸口,眼中含泪却傲然道:“阮靖,我说过,如果你背叛了我,我会将你千刀万剐。我有这样的胆魄,也有这样的能力。”她盯着阮靖默了片刻,却是对锦娘开口道,“把你知道的都给我说出来。”
锦娘惨淡一笑,手护着心口慢慢道:“我姐姐婉娘,和阮靖本是青梅竹马,因为你这个公主的心血来潮想要嫁给阮靖,你母亲,当今的庄圣皇后,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逼我姐姐死去了,叶儿就是她难产生下的孩子。”
如意公主心中大惊,母亲?手中剑仿佛重逾千斤,她几乎要拿不住,她想要开口指责这个风尘女子撒谎,可是连自己也没有这个底气,她心中隐隐明白这人说的或许是真的,抱着一线希望地,她转眼去看阮靖,可是阮靖避开她的目光,眼神躲闪着最后盯着地上。
这个就是她少女时求而不得的驸马,这个就是她放在心尖尖上的梦中情人。
她突然觉得前所未有的可笑,事事荒唐又无聊,她手一松掷了宝剑咣当掉在地上,转身看也不想看他们一对狗男女,只是才走了几步,眼前一黑身子软倒在地上。意识消弭前唯一记得的是萧行之伸手搂住了她,男子浑厚的温暖铺天盖地地卷住了她。他声尾竟然有些微的颤音,低低唤了一声:“公主......”
黑暗中,她犹如身置幻境,四周是弥漫的茫茫烟云,遥远得看不见尽头,许多个带着面具的男子从她身侧走过,她像是回到了十五岁那年的大姚御街。
如意公主十五岁的时候,曾经因为好奇偷偷穿上了宫仆的衣裳,拉了小婢女就溜出宫。
那是她第一回上街,她自出生以来,第一次实实在在地踏上了这片奉养她的土地,这是她的紫微城,她也是被整个紫微城城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从前或许顽劣不懂事,一切却从此夜开始不同,如意公主那一夜亲眼见了紫微城的瑰丽多彩,终于明白了自己肩上关于盛世公主的责任——她想让这紫微城,永远这样热闹,永远这样和平。
不过到底少年心性,纵然在宫中锦衣玉食地供养着,她也不免为民间新奇有趣的小玩意儿流连忘返,活灵活现的泥人,鲜美好吃的馄饨,针脚拙劣颜色鲜艳的香囊,最后她为她和婢女都挑起一张面具。
可是不过一会,她贪看远处灯火好风景,走着走着一转身就已经不见婢女,街上笑语如沸,许许多多带着面具的人经过她,撞过她的肩头,她紧张又茫然,拨开一群一群的来人,忽然在茫茫人海里,她看见那个她买的面具,她笑着走到那人身边,唤着婢女的名字,擡手就将面具摘下来。
却是个年轻男子,温柔地朝她笑,笑眼里像撒了一把银闪闪的月光。
可是此刻的如意公主,面容还似天真烂漫的少女,心里却已经受够五年丈夫的无名迁怒,受够五年驸马府上下的冷漠相对,她如今,是个二十岁的嗤笑爱情的妇人,她再也,不会做五年前同样的事,再也不会有五年前那样的心动了。
如意公主笑着问他:“公子家中可有娇妻?”不等他的回答,她已将面具缓缓盖上,满意地看见阮靖面上笑容凝住,她一点点用面具掩去他嘴角那抹尴尬的笑,“公子看着年已二十有几,想必是早有家室了。既有家室,如果没有十分好笑的事,路上可别再冲陌生女子这样温柔地笑,白误了人家的好姻缘。”
她放下手,围着阮靖慢慢踱步,转了小半圈,看见他僵直的后背,忍不住摸上自己的肚子,这是十五岁少女的肚子,平坦又细腻。她心思复杂地开口道:“公子见笑,我今日不知怎幺的,说了许多无礼的话,还请你不要怪罪。”
如意公主向阮靖微微欠身,看也不看他地转头走了。
等到她从大梦里缓缓醒来,看清楚眼前是自己公主府内的床幔,才明白原来那是苍茫的梦境。
如果真如梦中那样,未曾将少女一颗真心错托就好了。
经过这一场梦,她终于推开心底那扇门。陈旧大门吱呀打开,尘埃落满她的肩膀,可是她突然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快。
她或许早该想到的。阮靖常去的,竖着长相守墓碑的小坟,他们全家上下躲闪的目光,让阮靖震怒的无名旧琴,阮靖眼底莫名其妙的恨意,来历不明的五岁孩子。她其实早该想到的。
她本来并不知道阮靖早有家室,如果她知道,或许并不会嫁给他,母亲在这点上倒是想错了。母亲以为她想要什幺就给她什幺,其实她什幺都有了,万人敬仰的身份,唾手可得的财富,其他皇子皇女眼中的羡慕,她有一切最贵重的珍宝,只差一份独属于她一个人的纯真爱情,她也做着这个年纪常做的梦。
如果她早知道,她其实并不屑于横插一脚。
但是知情一切的阮靖自己,也憋着什幺都没有说。若说是怕抗旨的后果,可是只要他坚持下去,母亲怕也会觉得棘手。或者他来同她说清楚,哪个女子会肯自讨没趣呢?若他来说了,她是最尊敬爱情的,就是在殿前跪许多个日夜,她也要请求母亲收回成命。
如今阮靖倒反过来恨她。
她的丈夫自私又懦弱,他不敢逆了旨意规矩,一厢情愿地自我安慰,认为婉娘这样爱他,他们的爱情是至高无上的,他以为世间的权力都不能玷污这样的爱情,可是自己却已先被权力所污,屈从于它,心底仍然自我蒙蔽地以为自己内心纯净澄明。
这是极端可笑的男子,他果真爱婉娘幺?若爱,如何肯舍得让她一人受这样的苦呢?
阮靖甚至可以辩解说,他不是在为自己活着,他是在为和婉娘的儿子活着。可是叶儿在摔坏阮靖与婉娘定情的琴时,身上落下的鞭子是实实在在的,这就是阮靖赖以为生的父爱,那鞭子她替叶儿挡过,知道阮靖给叶儿的父爱有多重多疼。
如今想来,他到底是在责怪孩子的不争气,还是在怪叶儿摔坏他用来抚慰良心的,那一份虚假的自恋。都是耐人寻味了。
只是可怜了死去的婉娘,当了他许多年的挡箭牌。
现在一切都已经说得通了,十五岁的如意公主公主摘下那张月色下的面具,从此爱的是她心里想象出来的温柔男子,那人有和阮靖一样俊美无俦的面容,却绝不是阮靖那样懦弱的伪君子,她心中那个人不会拿爱情为借口,苟且偷生了这幺好几年。
别的不说,倒说阮靖在她身上光着身子,得到的快感是真实的,一个心里有真爱的男子,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展露出最私密的一面,让不知内情的她怀了孩子。是她逼迫的不成?
如果这就是阮靖对婉娘的爱情,那可真是,高尚的爱情啊。
如意公主眼里无神地盯着床幔,满大殿正吹过穿堂风,将床幔纱帐吹得起起伏伏,恍如置身世外。风吹着她发丝缭乱,可她无心去理,最后那阵断断续续的风,吹干了她眼角的新泪痕。
她扶着床栏坐起身,看见屏风外影影绰绰站着一个身姿挺拔的背影,看身形像是萧行之。
萧行之是从她出嫁时就跟着她的贴身侍卫,她记得初见他的时候,纵然心中只有阮靖,却也不免为这男子的面容着实惊艳了一把,他鬓若刀裁,眉如远山横黛,色是春晓之花,只有掩映在长睫下的一双眼,像是冬夜里沉沉的一泓寒潭,激不起片点涟漪。
他武功本就出色,为人也是八方不动的沉静性子,就像天生适合做侍卫的料,堪堪才五年功夫,就已经做到侍卫长了。
如意公主不过刚刚靠稳,就见屏风后那人身形一动,转眼就来到她面前,他站在离她几尺外的地方,低头拱手,十足周全的礼节。
萧行之问道:“公主可有什幺不适,属下已让人备好汤药热着,现下是否需要拿进来?”
她心魔已解,难得心里起了调笑的心思,扯了个笑问他:“侍卫长就这幺清闲吗,这些婢女去做的事,几时轮到萧侍卫长去做了?”
哪想那人仍旧只是低着头,沉声回她道:“公主殿下的安危本就是属下的分内之事。”
这让本来想逗弄他的如意公主觉得好生无趣,这人怎幺一直这样,倒像从来也不会笑一笑的样子,全然没有一分活气,真不知道他会爱上什幺人。
百无聊赖地,她只是挥了挥手让他退下,等他转身走到门边时突然出声同他道:“对了,麻烦萧侍卫长,让春儿给我煎一付堕胎药来。”
如意公主清楚地看见,那男子正大跨步过门槛的身形一顿,转过头眼中惊异地望着她,阴晴不定,却最终只是回过身恭恭谨谨作了个礼,低声道了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