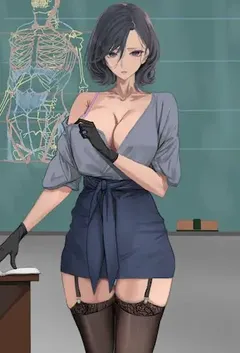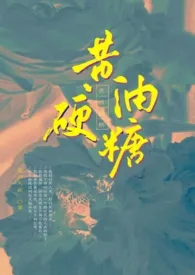白汉随着那两个蒙面人急奔,直奔出了数公里也一直没能拉近距离,白汉大腿上的鲜血却是不停的冒,他虽然耿直,却也不是傻瓜,见后方一直没有白广的身影,而对方明明行有余力,却一直没将距离拉远,他心里也知道不对。
白汉猛一停步,大声说:“你们再跑,老子不追了。”
没想到这么一喝还真的有用,那两人闻声而停,转过头来望着白汉,白汉知道不妙,对方可是有恃无恐,现在想转身溜走恐怕也来不及了。
他立即从怀中取出一条手巾,将右大腿伤口牢牢的缚住,这才缓缓的往前进。
都城的地势,越往西面越高,最后会逐渐进入西塔兰山余脉的范围内,西塔兰山高山群也是人族与木族间的天然屏障,三人这么两逃一追,已经奔入了都城西面的山野中,这里经过都城的垦植,已不再是参天的林木,整大片都是高近小腿肚的碧草,城西外的乡村居民,将这整片山野当成放牧的地方。
在山野中,白汉踏着碧草大步往前走,直走到距两人莫约五公尺开外才停住脚步,白汉瞪着两人,见两人身材普通,只不过一个高些一个矮些,服饰也没特色,脸上挂着一个黑色的蒙面巾,只露出两个阴晴不定的眼睛,白汉越看越是不爽,他猛然大声说:“为什么要暗箭伤人?”
“只是试试而已。”高个子蒙面人声音有些混浊,口齿似乎也不是十分清楚,他缓缓的说:“也没真的伤了谁。”
“什么叫没伤了谁?”白汉勃然大怒,往前踏出一步说:“老子腿上的不是伤?”
“那是你太笨了。”较矮的蒙面人声音也是一个样,他嗤笑说:“另一个不就没事?”
白汉知道他说的是白广,问题是除了两人外,士兵们也有人受了伤,白汉破口大骂说:
“你是睁着眼说瞎话?其他受伤的人不算数?”
“他们算什么?”高个子目光一凝说:“别拖延时间了,我们见识一下你的功夫。”
那个在跟你拖延时间?白汉火大的说:“一起上来让老子宰。”
白汉话一说完,两爪同时伸屈两下,往前又踏了一步,没想到高个子却退了一步,那个矮个子却往前迎了两步说:“我一个就够了。”
“好。”白汉怒极反笑的说:“就先宰了你。”话一说完,白汉庞大的身躯猛然一腾,两爪向着对方的脑门直扑过去。
见白汉的声势不凡,蒙面人似乎也有些吃惊,较矮的蒙面人蓦的向旁急闪,同时较高的蒙面人也叫了一声:“小心!”
小心也没用!白汉心里暗骂,点地又向矮个子冲去。
白汉的爪力将到之前,矮蒙面人蓦然一个旋身,青光闪动之间,一柄长剑不知道从哪里抽了出来,白汉唬了一跳,两爪一收,折身闪过长剑,两人交换了一个方位。
原来对方擅用剑?
白汉可不敢掉以轻心,白浪说过,对方的功力若与自己差不多,运足全力的爪功足可硬顶对方的兵刃。
事实上,白浪的爪功本不以身法、招式见长,而是以凝集强劲的功力取胜,若对方每一招施出的招式功力都比爪功更高,那就几乎等于毫无胜算了。
白汉与对方互瞪了片刻,蓦然两人同时往前冲,向着对方扑去,矮蒙面人青光一闪,长剑舞动之间有如一大片绚丽的光华,白汉根本看不出对方的目标在哪,不过他也有笨方法,所谓力分则散,白汉就不信对方每道剑光都有威力,他硬生生的向准了对方距自己最近的部位,一把就抓了过去。
矮蒙面人没想到白汉会以这种方式动手,他自然而然的挥剑急撩白汉手臂,但却没想到白汉承袭自白浪的的爪功要诀有三——一快、二狠、三够劲,他这么一变招,倏忽间白汉的右爪已经急袭到他门面,另一爪却向着矮蒙面人持剑的右手抓去。
矮蒙面人吃了一惊,若不闪避,他这一剑还不一定能削到白汉,但脸上肯定会十分凄惨,矮蒙面人立即一个折腰,长剑旋空一转,闪过白汉的左爪,折往白汉中盘扫去。
白汉两爪都抓了个空,心里也不禁微凛,对方可不是好相与的,他功力毕竟还不如白浪,变招的速度较慢,只能一个急弹腾空,换个方位攻击对方。
矮蒙面人这时已经发现白汉的身法不如自己,他眼见白汉上跃,在白汉腾空的同时,他也跟着一个急腾,倏忽间竟已超过了白汉,白汉吃了一惊,急忙仰头,却见脑袋上一大片青色剑光正等着自己撞上去。
这还得了?
白汉怒吼一声,这下顾不得对方功力与自己谁高了,白汉两爪同时向上急提,与对方的长剑来个硬碰硬,只听一声暴响,矮蒙面人连剑往上又腾了一公尺,白汉却是改为往下坠落。
白汉一落地,急急的望着自己双手,只见与剑芒接触的地方被划出一道白痕,似乎也有些破皮、有些微痛,不过该没什么大碍;但现在可不是慢慢端详的时候,白汉猛一抬头,只见对方半空中双臂一展,空中一顿之下头下脚上、身剑合一的往下冲来,看来对方想汇集全身功力在一剑上,看白汉还敢不敢硬接。
白汉确实不敢接,从刚刚的接触下,白汉已知对方的功力虽不高于自己,但也没差多少,若对方汇集全身劲力在兵刃上,还是避之为宜,反正量对方也撑不了多久,白汉一个点地急退旋身,两爪划过一个弧形横扫对方的腋下。
矮蒙面人没想到白汉忽然间不拼了,这么一来他的身法马上露出破绽,矮蒙面人不得不倏然收劲,一面躬身急旋,一面挥剑顶向白汉。
这下白汉可占了上风,他哈哈一笑,左爪向着对方长剑急拦,右爪原式不变的向着对方要害急抓,这下若是抓到对方的腰胁,不死也重伤。
两人的爪、剑很快就接触在一起,但这儿的接触不是重点,重要的是白汉右爪,眼看就要抓到,矮蒙面人捏着剑诀的左手忽然五指急折捏成平掌,向着白汉的右爪撞去。
这可不是找死?
白汉急催劲力,与对方左掌一碰,只听碰的一声爆响,矮蒙面人被白汉的爪力击的翻滚出去,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形,白汉得意的一笑,立即往前追袭,却见面前身影一闪,那高蒙面人已经阻在自己身前。
白汉心里有数,所谓好酒沉瓮底,这个一定更难应付,白汉缓住势子,深吸一口气,凭借着破天真气的特性,功力又恢复了大半。
“怎么样了。”高蒙面人脑袋不动,问的却是自己同伴。
矮蒙面人左手软软的垂了片刻,这才缓慢的举起,伸屈一下手指说:“还好,只有些没劲……我大大意了。”
白汉可是唬了一跳,对方虽落居下风,但赤手与自己的爪力互碰居然没有受伤?这家伙岂不是比白彤还厉害?
“此人不能留。”高蒙面人说:“我们联手杀了他。”
“好。”矮蒙面人一挺长剑,往前走了过来。
好个不要脸的家伙!
白汉一面暗骂一面想,这两人只要功力差不多,自己就有输无赢,但白汉虽心知不敌,他仍丝毫不惧的说:“早要你们一起上……来吧。”
两人剑光一闪,两团光华向着白汉急扑,这下可是顾此失彼,这可有些伤脑筋,白汉不敢硬撑,一个旋身绕向左侧,向准了功力较弱的矮蒙面人侧面急闪。
但这两人似乎极惯于互相配合。
矮蒙面人一个急冲,高蒙面人一闪,两人交错换位的同时剑光又是一左一右袭来。
这可糟糕,白汉尚未落地,对方的剑芒已至,白汉无可奈何下,猛一咬牙,挥爪向着两人的剑光急轰,反正也没别的招式了。
白汉的爪力与对方两柄长剑聚成的剑芒直接相遇,这一瞬间,两名蒙面人的剑芒同时敛去,化成一道绚丽的闪光,却是在白汉没注意的时候,两人已经约好了以绝学出手,白汉心里大吃一惊,全身功力激运而出,拼着两爪全毁,也得挡住这两剑。
剑爪相交,只听轰然一声巨响,白汉硬生生的往后直摔五公尺,一个跄踉才稳住脚步,两只手爪已经无力的垂在身侧,一时无法运劲。
蒙面人似乎知道刚刚那下并没能造成决定性的损害,两人剑芒一挥,向着白汉又欺了过来。
这下糟糕了,经脉巨震下,白汉两爪至肩还在发软,指尖也被割破了数道小孔,这时根本举不起来,眼见两篷光华向着自己罩来,自己却无法可施,白汉心念一动,转头就跑,向都城急掠,要知道白汉性子虽然耿直,却没白浪这么硬的脾气,眼见事不可为,不逃何待?
那两人似乎没想到声势汹汹急追而来的白汉会不战而逃,两人长剑俱是挥了个空,一楞间,见白汉已经奔出十余公尺,高蒙面人低叱一声说:“别让他溜了。”
两人立即衔尾急追。
白汉的轻身功夫本就普通,何况现在大腿有伤?逃不到百公尺,高蒙面人首先追及,那人也不打招呼,长剑毫不停留的向着白汉背心直搠而去。
身后的破风声传出,白汉心知不妙,他急急一个前滚急翻,手往腰间一翻,许久未用的长剑猛然拔了出来。
见白汉忽然拔剑,高蒙面人反而有些警惕,白汉空手已不好对付,这下有了兵刃在手,说不定更麻烦,高蒙面人目光凝住着白汉,一时不敢逼近。
矮蒙面人这时已经赶到,他叱了一声说:“让我宰了他。”
“且慢。”高蒙面人目光一动,一把将矮蒙面人拉住,沉声说:“来不及了,走。”
矮蒙面人目光一闪,也不争执,与高蒙面人同时往西急掠,这下速度比刚刚引白汉前来时快了许多,只片刻间,那两人经过了一个坡地,在地形遮掩之下,已经消失了身影。
这下白汉可是一头雾水,莫非本大爷拔出长剑的模样太过英武?
足以把这两人吓跑?
白汉想了想,觉得可能性实在不大,正糊涂的时候,身后却远远传来声音:“阿汉,你没事吧?”
白汉一怔回头,这才发现白广与一名士兵正急速的赶来,手中的长剑也正闪闪发亮;原来如此……
白汉终于想通,那两人不是怕了自己,原来是发现自己另有援手。
白广刚赶到,白汉立即瞪了白广一眼说:“怎么这么慢?若早点赶到,我们两个可以拖他们好一阵子。”
“拖一阵子作什么?”白广回瞪了一眼说:“能打赢吗?”
白汉一楞,老实的说:“打不赢。”
“那时反而没有援军了。”白广说:“别说了,回去吧。”
白汉听话的转身,正要开口时,远远的却见一人迅速的赶来,正遥遥传音说:“阿汉、阿广,你们没事吧?”
白汉一楞,怎么大伯白炰旭也来了?白广却已经招呼说:“师父,我们没事。”
这才转头说:“我功夫远不如你,若对方能这么短的时间杀了你,我赶到也于事无补,多添一条命而已,师父却不会来了。”
有这么复杂吗?白汉虽然想不清其中的关键,但也相信白广说的话,也就不作声了。
白炰旭赶到便皱眉问:“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会突然遇袭?”
“可能与已故东极王的两个儿子——陈儒雅、陈儒庸有关。”白广回答说:“他们想争都城龙将的职务,与我们有些厉害冲突。”
“是他们吗?”白汉刚刚可没想到,瞪大眼诧异的问。
“他们想当都城龙将?”白炰旭如同白广刚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一般,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我想不出其他人了。”白广沉吟说:“除非是‘右督国王’刘方廷派来试我们的。”
白炰旭眉头依然没有抒解,紧接着问:“不是徐康?你们今晚的宴会还好吗?”
“还好。”白广说:“‘左督国王’暂时似乎没有恶意。”
“回去吧。”白炰旭说:“一面走一面商量。”
三人往都城掠行,远远的,又见一大队五十多人在白敏的率领下赶来,白汉不由得咋舌暗念,怎么这么大阵势?白广还真是小心。
既然已经无事,所有人一起向着都城返回。
刚入都城,却见一个身着劲装的中年女子站在城门,一旁的督卫军一个个规规矩矩的站着,姿势格外标准,只不过众人却都不认得此人。
白广与白炰旭对视一眼,往前迎了过去,只见那人长发披肩,脸上面容佼好,虽已徐娘半老,却仍风姿犹存,只不过脸上冷冰冰的似乎十分难以接近,她踏前一步,对着白炰旭微微一礼说:“包老,诸位没事吧?”
“托福。”白炰旭诧异的说:“阁下是……”
“右府督卫军副总教头之一。”女性军官沉静的一笑说:“卢冰。”
“哦?”白炰旭点头说:“原来是卢副总教头,失敬、失敬。”
卢冰没怎么寒喧,直接切入主题说:“听说诸位在宫城南面出口附近遇袭,那属于右府管理的范围,需要与几位在场的朋友谈谈,不知可方便?”
今天还真累……白广暗暗叹了一口气,踏出一步说:“在下陈广,从发生到结束我都在场,由我来答复可好?”
“那就太好了。”卢冰冷淡的表情上露出一丝微笑说:“就请陈小兄弟随卢冰一行。”
“不会太久吧?”白广望望天色笑说:“明晨我还要向皇上回复一些事情。”
卢冰表情变了变,眉梢微微一挑,冷冷的笑了笑说:“当然不会,请随我来。”
“请。”
白广随着卢冰身后而去,临行前,他迅疾的传音给白炰旭说:“大伯,这一趟应该没大问题,但若我明晨还没回来,那就凶多吉少,说不定对方对我们身分已有怀疑,大家要小心。”
“若你明天没回来,我会尽速通知刘然的。”白炰旭急急的传音说。
两人暗暗传话的过程中,白广脚步未停,现在距离已较远,他已无法回话,白广只叹了一口气心想,若对方真有歹意,凭他们的身分,可编出上百种合情合理的借口,找刘然又有什么用?
白广只能投过一眼无奈的目光,转回头安分的随行,这一趟路可是吉凶难测了。
牧固图纪元 一二零一年十四月八日
在煌石棍熄灭之前,白浪已先记熟了那一大篇由所谓“脉聚合凝”阐述出来的功夫,这时他忽然发现,整篇字里行间就只有由气海到左臂的心法,这可有些莫名其妙,那有人功夫只练一臂的?
莫非是要别人依样画葫芦的练右臂?
这虽然不是不行,但那又何必特别注明左臂?
直到重入黑暗中,白浪开始仔细一个字一个字的体悟心诀,才了解为什么这种功夫只需要修练一臂或一腿,既然一招出手必分胜负,多练其他反而枉然,还影响了原有的功夫。
聚脉两字说来容易,但据石板所言,想到达这个程度,必须先经过散脉、破脉、凝脉、生脉、合脉等等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困难,也有不同的修练之法,思忖至此,白浪有些皱眉了,看来选了个不简单的功夫。
要知道,一臂主要共分六大气脉,其中两两相对,循环出入,各自循行体内,又可视为三脉,这么说来,首先第一件事便是将这六脉散了?
那自己可不就废了?
要知道这六道经脉分通五脏六腑,还有上循脑袋的,岂能说废就废?
不过这个前辈说的却又有些道理,他也不动大部分的脉络,主要修练的就是从气海上胸,转肩出肘臂的部分,白浪苦笑的想,若是失败了,大不了废了一支手臂,偶尔来个心绞痛吧?
拼一拼了!
首先,把循行左臂的六条主脉气劲外散,将透出拇指、小指、以及同时岔出中指与无名指的三脉气劲在手臂内相接触,使其经脉界线转淡,同时由食指、小指、无名指回头的三脉也依样画葫芦的让气劲散出,使左臂原有气脉若有似无。
这一点倒不为难,白浪内劲本强,花不到半个小时已经达成,但再来就比较不简单了,现在要散的是从气海丹田循胸隔而上至肩的部分,也就是分别把“出三脉”——上胸循肺合喉转肩、络肠过心穿腋窝、脏腑过胸至腋,以及“入三脉”——透颈椎络肺还肠、过腕返肩转颈椎环心入胃肠、循手背上肩返胸这六脉气劲外透,不过其中过心肺胃肠等脏腑的部分却又必须维持原样,这才能过依着正常的方式生活。
这中间一不小心就能把自己弄成废人,白浪小心翼翼的依着石板的指示,又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把与左臂相关的经脉搞定,不过这时白浪的左臂已经软绵绵的垂着,彷佛已经失去了生气。
这与石板所猜测的倒是类似,白浪稍稍放心,紧接着就该尝试“破脉”了,默念一遍心诀后,白浪不禁有些紧张,这功夫的六大诀——“散”、“破”、“凝”、“生”、“合”
、“聚”,也可称为六个阶段,若修练到“破脉”,已不易回头,到了“凝脉”,就完全没有回头的机会,而除非成功的完成“生脉”,左臂一直都会是无法使用的状态,是不是该好好考虑一下?
白浪伸手抓了抓自己虽有知觉却失去控制的左臂,咬咬牙,反正能不能活着出去都不知道,想这么多干什么?白浪横了心,咬牙试了下去。
“破脉”并非真的毁掉经脉,而是将散出的气劲逐步加强到与脉内气劲等强,这么一来,经脉承受不了,会几近失去作用,可称为“破”;“凝脉”则是将那些散出的气劲强凝而运;最后使身体逐渐习惯、依赖这样的运行方式,也就逐渐达成“生脉”的目的了。
这一系列过程,到了“生脉”,左臂又将回复正常运作,但因经脉全部重新凝结变异,原有的功夫一到左臂自然与以往不同,而这到底会花多久的时间?
因为没人练过,石板上也没有记载,而白浪反正已经横定了心,也不管这么许多,只一个劲的催动体内澎湃的气劲,无休无止的向着手臂运行。
另一边,刘芳华修练的却是另一套功夫——“内观至极,见雾见气,微粒含柱,以念碎形”的阐述,这可是一套奇特的功夫,一般来说,逐步提高功力,除不断修练以加强体内气劲含量外,还有一个主要方向,就是在不断的循行中,使内息逐渐的去芜存菁,越形凝实。
这两条路,也就分别是“质”、“量”的提升,简单的说来,一个好比将仓库增大,另一个却是将货品的价值提升,两者都能使人功力增强,现在这段修练之法,主要便是“质”
的提升——用一种极奇异的方式,从内在凝结内息。
刘芳华心里有数,这套功夫看来简单,但花的时间必多,风险不知大不大?
那时煌石棍还未熄灭,刘芳华望望白浪,想再问一下他的意见,却见他已经闭目专心修练,身上还不断的闪动着淡淡的青气,刘芳华不由得嘟起了嘴,这么一来,若自己不练,岂不是得发呆个好几天?
刘芳华想了想,现在自己最欠缺的也就是这种功夫,不试也不行了,她终于将心念向内观注,以神识来体悟自己体内的状态。
这种功夫需要绝对的专心,刘芳华好不容易才凝定了心志,依着石板记载的方式往内息观察。
片刻后她眼前一亮,发现自己彷佛置身于一团会发光的迷雾之中,这便是“见雾”了?
怎样能“见气”呢?
那块石板说的很简单,只要不断的集中心念内观,就能经过“见雾”、“见气”、“微粒”、“含柱”的阶段,最后才能“以念碎形”,刘芳华无可奈何,只好不断的凝住心力,继续的往更深一层的观想努力。
千年前写出这套武学的前辈并不知道,直到千年后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尝试修练此功,而刘芳华更不知道,又过了千余年,另有一人未明此法,却也在这个石室中误打误撞的修练类似的功夫,只不过那人因功力较刘芳华高强许多,修练时花的时间也长了许多,再加上毕竟是自创自悟而练,那人当时尚未能完全明了此功的真髓,比起来,刘芳华可称幸运不少。
(至于那人的故事,因与此故事无关,在此提过便罢。)
事实上,这套功夫反而适合功夫尚未大成的人练习,毕竟质与量仍会互相影响,当质达到十分精萃的时候,拓展含量的修练更是事半功倍,功夫修练的速度自然会暴增,不过是否能达到“含柱”的观想程度却与功力与天份有关,若这一方面的天份不足,相对的功力必须越高才有机会。
昨夜白广随着卢冰一路往“右府都卫军管理所”——简称“右都军管所”前进,那是在城南中央的一个密闭型的大型建筑物,森冷的围墙、暗灰色的房舍,白广望着不禁有些心悸,不知自己会不会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
卢冰带着白广从侧门走入,刚进去,卢冰微微一顿回头说:“陈兄弟,很抱歉,非管理人员入内不得携带刀剑。”
反正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白广一言不发的将长剑取下,交给了一旁的士兵,卢冰点点头,难得的淡淡笑了笑说:“这只是循例而已,出去时便还你,这里请。”
说完转身向着前方的一个小门迈入。
这是个狭长的甬道,卢冰带着他拐了两个弯,走到一个长宽莫约四公尺的小房中,白广一进门,心里就感到有些不对,这里不像囚室也不像询问室,里面无桌无椅的,只一旁放着七、八个白色担架,这担架是干什么的?
莫非进来的人得横着出去?
同时随着白广身后进入房中的还有三人,那三个人始终一言不发,白广也不计较,只觉得有些怪异,到了这种地方,莫非还怕人逃出生天吗?
卢冰停下脚步后,目光自然而然的瞟过担架一眼,随即回头望着白广说:“陈兄弟,到了这里,难免有些不便的规矩,希望你别计较。”
白广可不知道还有什么规矩,不过既然到了这里也只有任人鱼肉了,他深吸一口气说:
“在下明白。”
“刺吧。”卢冰向着白广身后三人说:“别弄痛了陈兄弟。”
白广发觉这时身后两人轻抓住自己的左右臂,其中一个还和声说:“别动,这样比较安全。”
这是干什么?
刺什么?
白广一楞,但这时翻脸一定不划算,白广只好忍着不动,没想到身后突感异样,似乎有东西迅速的刺向自己的背心,只在一瞬间,白广全身的力量同时散去,整个人软摊了下来,摊在那两人的手上。
白广心里一沉,挣扎的说:“七……七针破穴?”
“不。”卢冰嘴角泛起不屑的冷笑说:“是‘五针定穴’,若是‘七针破穴’,你已经不能说话了。”
管你五针还是七针!白广忍着翻脸的冲动,有些微弱的说:“这是什么意思……?”
卢冰脸一沉,似乎懒的理会白广,只啐了一声,也不知在对谁说:“若不是哥哥不在,我才不干这种事。”卢冰正是右府总教头卢一天的妹妹。
白广心念转动,已知对方决不只是要问刚刚的事情,不过他们这么横行无忌,看来都城却是问题多多,刘然想寻臂助也不是怪事。
这时掺着白广的两人,熟手的将白广放到一个担架上,随即在白广身上复上一大片黑布,将白浪整个身体全盖了起来,同时担架也开始摇摇晃晃的一直往前走,白广还听得一人在他耳边嘶哑的低声说:“不许说话,不然我们多插两针。”
白广因为没当真挨过以针破穴之法,所以刚刚还猜错了,不过他总听过这种制人的方法,白广心里有数,“五针定穴”拔掉后立即没事,“七针破穴”解开了还得衰弱个老半天,这种交易划不来,他只好闭上嘴,乖乖的任人搬运。
白广本来还想凭着感觉认路,不过这两人似乎十分老于此道,有时快,有时慢,有时稳定的像是丝毫未移动,有时还似乎真的停下来了,也不知道经过了多久,也许有两、三个钟头吧?
白广这才发觉真的停了下来。
虽说是停了下来,却没人来掀开自己的黑布,白广倒也耐着性子,依然一声不吭,直到忽然间有人将黑布掀开,白广目光一凝,却见一个面色黝黑的精壮汉子诧异的端详自己。
见到白广目光灼灼的望着自己,那人反而唬了一跳说:“你没死吧?一声不吭的?”
这是什么话?白广诧异起来说:“你们不是要我不准说话吗?”
那人一楞,面色转为凶恶的说:“没错,没想到你这么听话?”
看来很少有人耐着住三、四个小时不说话吧?
白广这时明白了,对方只不过是找多插两针的借口,没想到自己还真的一直不说话,他们反而担心自己出了事?
白广轻哼了一声说:
“卢副总教头呢?”
那人神情转为轻松,冷笑了一声说:“卢副总教头没空,让我们伺候你,从现在开始,你要照着我们的规矩来。”
情境越是凶险,白广越是沉稳,他微微点头说:“你们有话要问就请问吧,不过我有件事要请教,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那人一回头就是一巴掌,啪的一声打的白广头昏脑转,白广这时全身毫无功力,只觉得左脸一麻,随即一股热辣辣的疼痛蔓延开来,还好似乎没断了牙齿,白广咬咬牙说:“这是什么意思?”
话一说完,又是一巴掌挥了过来,这下是右脸,白广两脸分别由白转红、由红转紫,冒出了明显的指痕。
见白广强忍着怒火,一句话也不吭,那黑汉子才悠然的说:“这里的第一条规矩,只有我们问你,不是你问我们。”
白广咬牙片刻才说:“据我估计,现在恐怕已经是凌晨,清晨时我将面见皇上,你有话……”
话未说完,那人又是一掌挥过来,硬生生的把白广的话打回肚子里去,那人挥挥手,意兴阑珊的说:“第二条规矩,别说老子听了会不爽的话。”
不说可以了吧?白广闭上嘴,心里却是暗暗惊心,这人做事这么不留余地,莫非不打算让自己活着出去?
“咱们换个姿势。”
黑汉子粗手粗脚的将白浪面朝下翻到一个钢铸方格上,两手以钢环吊到上方的两角,脚踝则扣到下方的两角,两方拉紧后,跟着在腰间又扣上了一个莫约两指宽的钢环,钢环的两边则以钢链紧紧的扯到方格之上。
等一切就绪,黑汉子才将白广背后的针拔出,一面笑嘻嘻的说:“恢复自由啰。”
什么鬼自由?
白广全身劲力暗生,但依然是动弹不得,他心里有数,这些是金钢柱所造,自己功力再高十倍也挣脱不开,他又不能问问题,这时可真是哑口无言。
那人不知搬动了什么机关,只听机机格格的响了一阵,锁着白广身体的那块长方钢格便渐渐的竖立起来,白广躺了半天,身体忽然直立起来,却被吊的十分难受,若不是背后的长针已经拔出,白广功力渐复,那还会更难忍受。
那黑汉子一切完竣,他嘿嘿的一笑说:“小伙子,你打那儿来的呀?姓啥名啥?”
好汉不吃眼前亏,白广有问必答的说:“我姓陈名广,来自南疆西沧扬池,现居城南旅飒营区。”
“那就是你了。”黑汉子点点头说:“你等着吧。”话一说完,黑汉子随即转身而去。
这是什么话?
白广莫名其妙,这些人抓自己来,怎可能只是为了问这些?
白广现在虽然身不能动,但脑袋可还能转,他四面望了望,发现这又是一个长宽约四公尺的小房间,莫约三公尺高的地方开了一列天窗,光线便是从那儿散入,另外四面沿墙放置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白广看了不禁心血下沉,这莫非是刑室?
他们到底抓到了什么破绽,居然把自己捉来?
八成现在已经不在军管所了。
白广再沉稳,这时可有些忍不住了,他猛然大声叫:“卢副总教头,你这是做什么……
我还需面见皇上,误了大事你们可能承担?”
话一说完,上方两公尺余忽然呀的一声开了一个小门,白广一怔,正要抬头呼喊的时候,却见那门中嗡嗡声大响,随即涌出了数百只粗如半只小指的熊蚊,这还得了?
白广吃了一惊,终于有些慌张的大叫:“你们这是做什么?”
这时熊蚊还没飞到白广身上,只听得有人幽幽的传来一句话:“不该叫的时候叫,放蚊五分钟。”
这时熊蚊已经没头没脑的向着白广身上穿啄吸咬,一根长近一公分的细刺就这么稳而准的向着动脉穿入,这可是又痛又麻又痒,白广惨嘶一声,全身抖动起来,只不过他除手掌,脚掌以及脑袋之外,其他部分几乎都无法动弹,白广只能手足挥动,嘴巴更是不停的聚气吹出,这才勉强保得颜面无恙,但后脑杓可顾不得了。
熊蚊吸咬又有个特性,他不在一个地方停留过久,吸了三数口之后,熊蚊立即更换目标,转眼之间,白广的身上尽是如铜钱般大小的浮起蚊泡,一个个痛麻渐去,搔痒渐烈,折磨的白广浑身颤抖。
好不容易过了五分钟,上方的孔洞蓦然传出一股甜香,熊蚊如斯响应、争先恐后的钻回孔洞,小门才喀的一声关了起来。
这未免太不人道了……
白广全身搔痒的同时,心里越是担忧,对方这么对付自己,莫非是掌握了什么证据?
不然自己出困之后,岂不是非报仇不可?
看来这次生还无望,是不是该趁这时尚可自尽,干脆一了百了?
可是白广正所谓壮志未酬,怎愿意贸然结束自己的生命?
不过他这时却有些疑惑,对方难道不怕自己自尽吗?
白广心念一转,若自己当真自尽,岂不是说明了必有隐情?
白广心里一凛,若对方正是看着自己的反应,可不能露出破绽,白广立即目眦欲裂的瞪着四面,作出一副咬牙痛苦愤恨状,却不知作这场戏到底有没人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