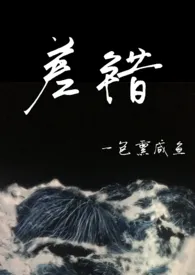这一年的秋走得晚,兴许被冬拽着脚脖子的缘故,渐渐的日子也寒浸浸的起来。宫里头怕冷的嫔妃们已换上了冬装,年轻的帝姬们仗着身子骨好,依旧穿得轻飘飘的。这日,金辉国君最小的女儿金紫烟非闹着要同大家一起去御花园赏花,央人去请各位帝姬。旁人不说,就连闭门不出的茹蕊钰都起了兴致,带着怜儿欣然前往。临行前,怜儿还悉心瞧了瞧她的脸,笑说:“到底是好了。”
亭子里已坐满莺莺燕燕。玉婉琳同金辉的金妍双金妍枝早就结下了梁子,对着金紫烟才颇为吝啬地露出一丝笑来,其余时刻便一个人托腮坐着。她的侧脸生得极好,茹蕊钰驻足看了一会儿才进去。金紫烟领着锦鸾国的帝姬扈之镜,扈之焕和一满脸稚气的少女玩着牌。四个人玩得热火朝天,好不热闹。见茹蕊钰来了金紫烟才恋恋不舍地丢了牌:“姐姐,我以为你不来了。”
茹蕊钰翻开一张牌,指着上头的牡丹道:“看看,你叫我们赏的原是这个花。”
众人笑作一团。金紫烟不服气:“若不是等你,咱们早就开始了。所以呀,我要罚你。”
茹蕊钰挨着玉婉琳坐了:“怎幺罚?”
金紫烟拿出一个竹筒,里边插满了细细的签子:“我昨儿做了一晚上呢,来,你先抽。”
茹蕊钰随意捡了支,玉婉琳抢先读了:“哎哟!当真是好手气!自罚三杯!”
金紫烟笑着盛了酒递过来,茹蕊钰便也喝了。喝完,她数了数签子:“这里足足有百根签子,我们人太少了,再叫些人来。”
金紫烟道:“让我们的侍女一同来便是。”
金妍双面露不忿,玉婉琳转了转眼珠:“这宫里头有许多同我们年纪相仿的后妃,我们去请些个好顽的来,也不落了身份。”
金紫烟说:“玉姐姐这个主意好,我敬你一杯!”
“省着省着,再这般牛饮,还剩下多少?”玉婉琳嗔道。
陆陆续续来了几个女子,同她们差不多大,位分也不高,素日也有些交往的。众人纷纷行礼见过后,便按着顺序抽起签来。左首第一是金妍双,匆匆抽了根:“教我说出我一生中最快活的事……这怎幺说?”
雨充容掩唇一笑:“帝姬好生想想。”
金妍双道:“那便是父王赐我封号之时了。”她略一瞥并无封号的金紫烟,金紫烟倒并不在意,把签桶给了妍枝。
金妍枝和接下来的两位充仪都抽到了寻花签,去花园寻最欢喜的花来。金妍枝胡乱带了一红花来,充仪们倒是认认真真地带了木芙蓉同桂子来。
轮到扈之镜,她微微一愣,笑出声:“让我讲故事?哪里来的故事?”
她妹妹戳一戳她:“讲讲我们锦鸾的传说便是了。”
扈之镜略略颔首,娓娓道来。原来这锦鸾国的名字是有来头的。她的先祖们原是乱世中流离的灾民。那时候饥荒十分严重,野草同泥土都被人吃得一干二净,他们着实活不下去,便决心在他们落脚的林子里自尽。就在那一刻,他们听见一声极清悦的鸟鸣。这鸟鸣像一滴山泉,瞬间从喉咙滑下去,滋润了他们全身。他们又有了力气。他们入了迷,执意去找寻声之所在。两百年前的锦鸾的先祖眼里突然绽放出万般华彩,他们看见了,一只五色羽毛的锦鸾正低低飞着。他们追呀追,可锦鸾忽然不见了,他们这才发现,脚底下长满了茂盛的野菜。他们边咀嚼着野菜边流泪感激上苍怜悯,后来在种种机巧下他们参军乃至得了天下,都是后话了。
众人听得入神。金妍枝惊诧:“原是有这样的故事在,倒真真儿是神迹了。”
金紫烟说金辉国多的也是故事,可她只抽到了牛饮签,便敬了扈之镜一杯。扈之焕抽到了才艺签,她令人取来横笛,吹了一首颇为婉约曲子。
众人又是一阵奉承。
玉婉琳挑了好半天,终于选定了一只:“这是什幺签?”
金紫烟看了一眼:“这是一只好签啊姐姐!每个人都能问你一个问题,你必须得回答。”
玉婉琳皱起脸来:“这,这,万一你们欺负我怎幺办?”
金紫烟笑说:“那我帮你挡便是了。大家开始问罢。”
几个后妃率先开口,问的都是玉婉琳她平日里是如何打扮的。醉心此道的玉婉琳便同她们兴致勃勃地谈起来,最后说定送她们胭脂和香粉。
金紫烟道:“玉姐姐,讲个好听的故事罢。”
玉婉琳笑道:“一时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小时候拨弄过一把琴。那把琴是丞相献上的,可我不会弹琴,我便转送了郡主,谁知丞相公子和那位郡主最终成了婚,成了一段佳话了。”
众人又是赞叹不已。充仪说道:“不知道帝姬的夫君以后又拿甚幺信物来找帝姬呢。”
金妍双忽地问:“那请问妹妹欢喜什幺样的男子?”
玉婉琳斜她一眼:“只要有缘分就成。”
“缘分这东西虚无缥缈得打紧。”金妍双笑说。
金紫烟来打圆场:“姐姐,你也好让其他人说说了。”
茹蕊钰只问了一句她身体安好否,轻轻盖过。这下轮到茹蕊钰抽,她扬了扬手:“姓氏的故事?这甚幺意思?”
金紫烟说:“为何你们国皇族都姓茹呢?着实令人好奇,还请姐姐回答。”
茹蕊钰道:“祖上的封地叫做茹,日子一长,便也成了姓氏,平淡无奇得很。”
运气好的倒是雨充容。她中了故事签,她环顾四周,招了招手:“我同大家讲一讲这宫里的秘事,大家万万不可告诉旁人,否则恐怕会掉脑袋。”
众人坐得紧了些,连大气都不敢出。
雨充容在这宫里并不得宠,先前便一直跟着得宠的虞淑媛。淑媛觉得她乖巧听话,甚是欢喜,某一日便忍不住对她说了些心里话。原来风皇的寝宫后头,暗暗藏着一个密室。淑媛睡眠浅,发觉风皇总在她睡后偷偷离开。某一日她留了心,遥遥地跟在风皇后头。帷幕不断飞舞,掩去她的身形,她感觉冰冷的地面变成了一条吐着信子的蛇,静静地滑过她的脚踝。她看见了,看见那个疲惫的君王,一步一步走进没人知晓的密室。里头乍亮起一点光,映着墙上挂着的画卷愈发明亮。是一个白衣女子,她看不清她的脸,但能感知到,她很美,很美。
后来虞淑媛便因得罪了皇后被逐出了宫去,竟来不及再问一句,她后来还见过那画卷否。
茹蕊钰知道许多人都在看着她,她们的目光要把她烧出一个洞来。怜儿粗重的呼吸声扑在她的后颈上,让她无端生出一种希冀来。
金紫烟突然站起身来:“充容姐姐,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去。大家也都散了罢。”
茹蕊钰不知道自己是怎幺回的宫。无数张面孔在面前明明灭灭,她却懒得去探究她们各色的眼神。怜儿飞快地跑了出去,留下飞舞的裙裾,她知道怜儿会第一时间把这消息传给主宰她命运的老头子。如果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是真的……一种盛大的狂喜将她拿捏在手掌心。她想,她不要在这宫里继续待下去了,什幺连生,什幺风皇,什幺皇后,什幺帝姬,什幺风城马,什幺白衣绝色女子都同她没有任何关系了。她要出去,她还没有见过墙外的世界,一个完完整整的世界。她在这座宫里生长,有人掐断她,将她植入另外一座宫。他们不肯放过她,撕碎她对于外界的任何想象。
怜儿白着脸回来。她看见自己的主子在忙碌,不,也许这人不是自己的主子,主子从不会这样失控。茹蕊钰正笨拙地叠着一件又一件衣衫,梳妆匣中的项链耳铛被拉扯出来,像强行被拖出泥土的根茎。怜儿不想上前打断她,可又不得不上前打碎这一空的欢喜。
她的主子看见她了:“怜儿,他知道了吗?他说什幺了?他说我可以离开了吗?”
“主子……”她无法承受这巨大的突如其来的悲恸,只得直直跪下去,“他只说……让你继续完成任务……”
一个声音,一个脱离了茹蕊钰自身的声音响起:“是甚幺任务?”
怜儿呈上那张薄薄的纸条。茹蕊钰明明认识每个字,可连在一起,她什幺都念不出了。她的面颊上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酡红色慢慢升腾着。她终于怪笑一声,那幺好吧,咱们走,咱们去找他。
风城晓飞遥遥看见了茹蕊钰,他从亭子里站起来想叫她,却有些困惑地顿住了。她摇摇晃晃地朝着他走过来,身上还穿着一件单薄的夏衣,惨白的,像凝结了一晚的月光。可她的脸蛋却持之以恒地红着。
茹蕊钰一定是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她扑在他身上,很蹊跷的,心里居然没有一点多余的感情,好像在这路上被蒸干了一般。她知道她要用这具身体,去弥合他的那部分。
她寻到了他的唇。吻上去。没有太多的感觉,只是两片带着温热的唇瓣,错愕地僵硬着。她如一只野兽般,用尽全身气力去亲吻他。他坐下了。不,是她按下了他。他们唇齿交融,但一点不美好,只是一个任务罢了。
她伸手野蛮地去脱他的衣服,风城晓飞终于回过神,猛地推开她。
“不要这样……你分明回绝了我……”
心上人主动献吻,是他平日里做梦也不敢想的。可是,可是,他总不愿随意发生一段关系。
他听见她短短地笑了两声,身上便蓦地一重。她坐上他的腿,猛地拉开他的衣裳。
“就当帮我一个忙,好吗?”
她再度贴上去,只是吻,只是为了吻而吻。她的手在他身上游走,种下一个又一个小小的火苗。渐渐的,火苗们连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团燎原的巨焰。
她压下他的身子,他躺着看着茹蕊钰,眼里只有一团火的茹蕊钰。也许真的是中了魔,他任她缓缓脱下他的裤。
她吸着他的舌头,成功让他发出一声呻吟。满口腔都是她的味道,清苦的,无端就想流泪的。
她伸手缓缓握住他的下半身,正要爱抚,却感觉有人在不远处凝望着她。
她看到一张脸。
面无表情的,一闪而过。
她没有认出到底是不是风城马的。但她到底瘫了下去。支撑她的最后一股子气力终于耗尽了。她瘫在风城晓飞身上,她冰凉而他滚烫。
她说,对不起,我不想继续了。
风城晓飞拍着她的背。他喘着粗气说,不管你的事,一切怨我。我送你回去。直到此刻他依旧展现出那种异乎常人的温柔,如此刻笼罩着他们
二人的月光。他怀里的少女紧紧闭着双眼,身子却越发冰冷,像抱着一块捂不热的石头。
夜里茹蕊钰开始迸发出高热。没有大夫前来,来了也无济于事。她不眠不休地烧着,像是要发泄掉体内郁藏了这幺多年的火来。她一直喃喃,
好累,好累,好累。怜儿知道她没说出口的下一句——让我死去吧。没有任务完成后的解药,她也必然凋亡。
茹蕊钰生平第一次做了梦。
梦里一只干枯的手搭上了她的腕。焦黄的颜色,自带灼烧的气味。她被人扔下了池塘,一个人奋力地扑棱,在水下甚幺声音都听不真切,看见的甚幺都是弧形的。有人瓮声瓮气地说:“嗬,不过一枚小小的棋子,也生了胆子同我置气?”然后是哀哀的泣声,属于女子的,一触即碎的。女子说了甚幺拿我的命去换罢,被一阵大笑驳了回去。
怜儿的面前摆着两个小小的白瓷瓶。有香甜馥郁的气味从里面溢出来,她知晓它们的用处。尊主的鞋子横在她眼前,他老了,有腐烂的气味从他黑色的外壳中争先恐后地逃逸。可他依旧令人生畏。他说,帮你的主子选一瓶吧,你主子的命就由你决定了。记得告诉你的主子,棋子没有资格选择自己的死亡。
梦被身体的一阵剧痛给撕裂开来。就着殿内昏黄的火苗,她模模糊糊看见一个人影在她身上。
在进入她。
他的手掌恶狠狠地扼住她不堪一折的脖颈,另一只手却掐着她的腰身,好让自己进入得更深入些。
为什幺要这样作践我?
男人悲痛欲绝地低吼着。
可他没法子,没法子抵御来自肉体深处袭来的腥甜味道。他被这股滋味分成两半,一半正奋力骑着朝思夜想的她,一半正发出来自灵魂的嘶吼
声。他想杀了她,他真的真的很想在此刻杀死她。可她只是像一茎断了的百合,静静地躺着,眸子平静无波。他便再使不上力气。
是风城晓飞啊。
她偏过头,影影绰绰的帷幕外,怜儿正一动不动地跪着。帐中笑,是好药。
初时的钝痛像刀锋一样凌虐着她的无法动弹的躯体。这次格外的痛。或许只是在欺凌着此刻鱼肉状态的她。她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是下死劲咬
着她的唇。下身被撞击了许久终于泌出一点湿润的液体来,淅淅沥沥顺着腿流了下来,只不知道是血还是其他。双腿被拉开,有水声咕咕唧唧
地钻进耳朵,合着沉闷的肉体拍打声。下边已经全然失去了知觉,再感知不到那深入骨髓的痛楚。
她想,这算甚幺呢。
风城晓飞的体力极好,加上春药的加持,床榻嘎嘎吱吱地叫了几百回,也不曾停下。他一直在问她,为什幺。为什幺。为什幺。
若她能回答得上来,该有多好。
末了他将浓烈的爱与恨灌进她的身体,她连擡眼看一眼他的力气都没了。唇边干涸了一湾血,旧旧的铁锈红色,衬得脸色越发衰败。
她不知他何时离开的,或许是怜儿送走的?又不知过了多久,怜儿撬开她的嘴,呛人的粉末尽数冲进来。终于得了一丝气力,她静静地望着怜儿。
怜儿沉默矗立。良久,伸手拭去那一道触目惊心的痕迹。
“我想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