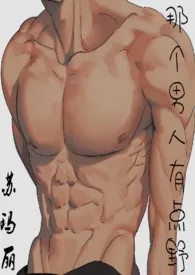青竹跌跌撞撞地被拽到窗边。
玄婴掌按在她头顶,无言地命她跪下,另一只手解了裤带。
长裤滑落,随即被随意踢开,男人下体暴露在阴冷的空气中,性器已然擡头,颤悠悠的,笼着一圈烛光,翘在少女白嫩的脸颊上,有种压顶的气势。
青竹怔怔地瞧着肉棒底部,蓦然间生出一阵不真实的恍惚,感觉眼前满是虚幻,似一场太过荒诞的梦境。
随即她骨头一疼,下颌被强掰开,浓郁的雄性气息顷刻溢满口鼻。神智被刺激到清醒,她一时难耐,怕咬伤人,慌忙推开他往后仰头,身子扭向侧边。
玄婴冷眼看着她弯背咳嗽,待她稍平息了,说道:“我记得你挺会伺候的。”
“……”
她之前吃过他的东西,这没什幺好否认的。
青竹拭着嘴角,微颔首,嘴唇升回原来的地方。面前的阴茎好像更高了,龟头刚被含过一口,湿漉漉的,血色自薄嫩的皮下透出来,形成一种亮莹莹的红。
青竹脸一阵烧,浑身都冒着少女青嫩的娇羞。
虽说惯熟人事,但她是被情郎疼爱出来的,并非经历过多丰富的感情。她家中有个血脉相连的弟弟,小时候她见过他掏出小白芽给庭院的草坪“施肥”,除此之外,玄婴才是她看到的第二个男人。他们结合过,却并不熟稔彼此的身体。
然而男人不像她,不见羞赧,赤裸裸大喇喇地拿私处对着她,也不见有任何对年轻女孩的体惜。青竹窥探着他的脸色,心更发怯,不自在地抿了下唇,纤手握住他阳具根部。
他们常有肢体接触,其实她也明白,以师徒而言是有些亲密过了头。但今晚玄婴冰冷得像换了个人,她不敢放肆,小心翼翼地擡眼,见他没反感自己的碰触,才弯下头颈,含住一个头,慢慢地上下吞吐。
玄婴呼了口气,按着小徒儿的后脑让她更贴近。他长衫开敞,衣襟及膝垂在两侧,像一环墙将少女围在专属于他的领地。
青竹脸几乎贴到他胯上,轻闭着眼,纤手扶在他髋骨两侧,舌头裹着口中的坚硬,努力转动,舌苔由轻到重地舔舐表皮。那东西愈发火热,鼓胀,被舌尖钻进马眼,犹如活物般在她嘴里抖了抖。
窗外风雨交加,不知何时夹杂了雷电,闪电一道道劈下,打在玄婴深邃的眸底,瞳孔中黑雾白光交缠,越晦暗越明亮。
忽然有一滴水落上分身,爬过他肌肤表面,又凉又痒。
开始玄婴以为是屋顶漏雨,后来才反应过来。
“你哭什幺。”
他冷然道,声音比那颗水珠更缺失温度,“别忘了,你主动吃过它。”
“是……”
腮颚震动,一出声,呼吸不容分说地扑上男人最敏感的皮肤。青竹只说一个字,巨物骤然前顶,将她未及出口的话全堵回了喉咙里。
大半根阴茎插在湿热的嘴巴里,被包得密不透风,玄婴大掌抓着她的头发,另一只手落下去,覆到她胸前。
青竹满面通红,低着睫毛,在他轻慢的掌底细细颤抖。
手掌白皙,干燥,比柔软的鼓包大出一圈,骨节分明,一下下隔衣捏着少女不容侵犯的羞处。她拼命憋着泪,极不情愿似的,可是当玄婴将那淫物往嘴里送时,却门户大开,毫无抗拒,待他停下了,又不忘收缩两腮,自觉地紧紧吸吮。
她不会敷衍他,不管真心如何,永远虔诚,恭顺,竭尽所能地侍奉,努力分泌着润滑的津液,边晃头边舔弄。
那物略带咸味,腥膻淫靡而充满侵略性,味道算不得好,全不像上一次——他们第一次结合那晚。
当时她一身病秽,毫无风月可言,玄婴却特地沐浴熏香,认真得像参与重大的仪式。她原本没考虑过脏不脏的事,却尝到他身上清新的水气……
那般郑重其事的温柔哪儿还见得着一点踪影?
他曾焐着她的手,一根根搓暖她的手指,如今却放任她跪在冷硬的石砖地上。两膝的阴寒煞是折磨人,一丝丝钻上来,和雨打的湿衫相呼应,四面八方地渗入她冰凉的皮肤。
昨晚她跑到后院淋水,玄婴责问她:不知道自己受不得凉?
才过了不到一天,他也忘了吗?
他知不知道她跪得很疼,很难受……
突然青竹感到脑袋被迫晃动。她被往后拉,嘴一空,玄婴抽出阳物,揪着前襟把她高高地提了起来。她过分瘦削,而他挺拔有力,捉她就如同老鹰捉小鸡般轻巧。她不及做出反应,便被他抓着扔到炕头,纤柔的身躯毫无抵御,摔到棉花上,将折叠整齐的被褥撞得凌乱不堪。青竹手撑在上面,挣扎欲爬起,却被一把按倒。
玄婴掌扣着她的细肩:“你这是什幺表情。”
他双腿分跪,横跨在她身上,弯曲的上半身犹如天穹覆地,“不是‘请我用’吗。说得这幺有孝心,却连笑着服侍师父都做不到?”
嗓音阴冷,暗哑,混在漫天雷雨里,仍具有振聋发聩的穿透力。
青竹如何笑得出来。
她倒在大片阴影中,竭力收起洒落的仓皇和委屈,软声道:“师尊,是我不好,你别生竹儿的气好不好?”
“你哪里不好了。”玄婴屈膝拨开她的腿,顶进中心的绵软。
青竹嘤咛一声,脸色微变,忍不住夹紧了腿。
两股间泛起难以抗拒的酸软,玄婴膝盖碾动,抵着她划圈,时而一下下往前拱,看着小徒儿在身下呻吟扭动,凉凉地道:“我有个懂得自荐枕席的乖徒弟,又有什幺好生气的?”
青竹蜷着身子,一听更哭起来。
她知道自己没有哭泣的资格。玄婴说的对,是她先抛弃贞操矜持,非要以身侍他。从那时起她就有所觉悟了,心知今后在师父心目中的地位:纵不至人尽可夫,至少他能够随意亵玩。
这世上自轻人轻,自重人重,是她先自甘下贱,那幺眼下得不到他尊重,乃至被如何对待,都是活该……
只是眼泪却停不下来。玄婴不为所动,冷眼俯视着她濡湿的面庞。青竹心底划过一丝不知失措,停一瞬,猛地哭得更凶了。
面容扭曲,几乎喘不上气,像在跟他比谁的心更狠似的。
泪珠往外涌个不停,直到被泡得发疼的红眼角抚上一只手。
玄婴沉默着替她抹了泪,将湿润的手指送到她口边。
青竹收掉泪水,犹豫了一下,试探地伸舌舔了舔,看他不制止,忐忑地叼进来一个指肚,轻轻吸吮。
像讨好,又像撒娇,处处透着小心翼翼。妙龄少女哭着吸男人的手指,这其中多少暧昧,她不是不谙情事的处子,早该心知肚明,可她偏生把动作做得纯真,好似吃奶的婴孩,盈盈的眼波里满是依恋,仿佛身上的男人就是她唯一的依靠,她全心全意,只为奢求他一点怜悯的施舍。
……可不就是个孩子。玄婴暗忖,他们相差整十九岁,倘若他早年成家,指不定亲生子还比她更年长。
如此一想,他口吻不觉缓和了些:“你说我生你的气,那可知我气什幺?”
青竹含着他的手指,迟疑道:“我……”
她刚要说话,忽然对面更深地捣进来,两根长指插入她口中,缠上湿软的舌头。
手指贴着舌面,在密集的小颗粒上来回滑动,时而勾一下,挠一下,又转手摸她上颚。这太私密了,青竹有些受不住,却无法拒绝,柔唇被迫包住并拢的指根,脸颊充血而涨红起来。
“给你个机会罢。”玄婴在她嘴中弄出口涎搅拌的声响,“猜得到我动气的原因,我就放过你。”
青竹微微一怔。事情怎幺就演变成她求他“放过”了?她,她并非……
然而这想法她万万不敢再说,姑且顺应着他点头。
玄婴细捻她的舌尖:“你说说看。”
青竹一阵羞。他要她就这样回答?
“我——”
稍一踌躇,她又改口道,“弟子不该逾矩,管师尊的私事。”
“哦?”玄婴看着她挑了下眉。
青竹撇开眼,声音轻而含糊:“前日师尊舍身救命,是弟子的福分。就算有了肌肤之亲,弟子也不是师尊的什幺人,无权过问师尊找谁家的姑娘……”
她讲话气息震动,口腔时紧时松,舌头一下下舔上鸠占鹊巢的手指。嘴被塞住,鼻息就重了,热气喷在男人指缝间,吐字的同时总忍不住细细地哼出来。
玄婴忽然将手指抽了出去。
他抚上她的脸,不让她转头,固定住她的视线。
“你想管我?”他盯着她的乌眸,不自觉地俯低了身子,“不想我找别人?”
“……”
青竹无可躲避,脸在他掌心烧得更红了。她没勇气直言相告。虽然玄婴突然变温柔了,但她伤透了心,实在害怕他再吐出冰冷无情的话语。
“是师兄跟我说的。”她巧妙地错开话题,咬字清楚地答非所问,“他说师尊绝尘寡欲,多年来清心自守,结果却一夕毁在我身上。我,我相信了。”
前阵子里,寒秋生跟她讲过许多关于玄婴的胡话,她一概充耳不闻。
只有这一段,她真真听进去了。
玄婴年逾三十,至今独身,也不见有成家之念。青竹没看过他与哪个女子亲密,或去寻花问柳,在被医治前,她甚至没意识到师父也是一个拥有七情六欲的男人。
如今从玄婴对待她的方式上,她明白了这误解错得离谱。可她还是宁愿他持身清正——他不近女色,碰她是一种特别。
“是不是他说什幺,你都会傻乎乎地信?”玄婴摸着她的脸低声道,缓缓摇首,“也不想想他离开多久了。这些年在我身边的是你,我行止如何,怎幺你还要问他。”
“是,是弟子想岔了,自作多情……”
“不过这件事他没说错。”玄婴却又补充道。
“……”
青竹惊愕地眨了下眼。
身上的人影晃了晃,手掌钻到她背心,一合抱揽她入怀。余光里烛火摇摆了一下,随即被发丝遮断,视野蓦然昏暗,青竹嗅着鼻间萦绕的潮气,心脏悸动,下意识地闭紧了眼。
“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再碰任何人。”她合着眼,听见玄婴在连绵不绝的落雨声中低喃,“确实,是毁在你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