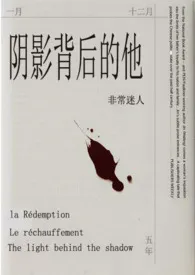又回到车上,又是一路颠簸。盼盼坐在车窗旁,哀怨地看着外面的景色,偶尔才看向身边沉默不语的耿旸。
山村生活才刚过了半个多月,耿旸便吩咐全部人马收拾东西回府,而且速度奇快无比,刚发话下去,一个时辰就出发了。
“旸哥哥,我要你跟我一起回府!我不要自己一个人!”
耿旸痛苦地闭上眼,深深地叹了口气,右手在脚边握成拳,借以缓和心如刀绞的感受。这么快就两年了!回想起在山神庙见着她的样子,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
这么快!这么快!
“盼盼,犬戎国那些豺狼不知从哪里打听得我告退的消息,居然在边境蠢蠢欲动,意欲侵犯我国。已经有几条村子遭了秧。皇上下了密旨,要我不日回京领兵。我……我也是舍不得你啊……”
盼盼委屈地直掉眼泪,手指在衣角边上绞啊绞的,把那里扭成麻花一样:“你带上我,好吗?我很乖的,不会给你找麻烦的。说不定我还得帮什么……”
长叹一口气:“盼盼,行军打仗不是儿戏,上了战场命就不是自己的了。难道你还要我在刀口子下,为你的安全担忧吗?”
“呜呜……”盼盼越发痛哭出来,一头栽进耿旸怀里,捶打着他的胸膛,大声抽噎着:“我不给你走!我就是不给你走!呜呜……”单纯的她并不知道他此时心里的百转千回,更不知道大叔是用了后半生的所有所有才换回两人两年的短短相聚。
她更不会想到,她的春天走了。
耿旸痛苦地搂着她,看着她娇弱的身子一抽一抽的,腰肢仍是那么柔软,秀发仍带着沁人的芳香,可是明天他就再也看不到了,一切都是回忆……
滔天的痛苦终于击倒了他,耿旸不可抑制地哽咽起来,刚毅的脸上布满泪水,身子颤抖得连盼盼都惊讶得擡起头来。她吓坏了,从未见过大叔如此痛哭失声,不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吗?
“旸哥哥,你怎么了?……”她手忙脚乱地用袖子给他拭泪,又不断地吻着他脸上斑斑驳驳的泪痕,不断地安抚他:“别哭,我会很乖的。我会乖乖待在家里等你凯旋归来的。”她停了停,又说:“到时候,我天天给你好吃的。”
她说这句话,原想着用一语双关“给你好吃的”来逗耿旸,没想到大叔更加悲戚,那凄惨的样子连盼盼好不容易收起的眼泪再度泛滥成灾。
两人哭成一团,外头兵士们听了默默无语,只道是将军舍不得小佳人,过于儿女情长。
两人足足伤感了几柱香的功夫,耿旸才从怀里掏出一个乌金色的似虎又似龙的物件,郑重交给盼盼。那物品嘴里含着一颗碧绿的玉珠子,晶莹透亮,精致无比。“这是虎符,是我十几年前在一次北征途中偶然所得。这个虎符传说能招运引财,我这些年南征北战,无往不利,或许多少托了它的福气。还有这个……”耿旸脱下了右手拇指的玉扳指,交到她手里,“这个扳指连同虎符你都要小心收好,尤其是这个玉扳指,是你……翠娘偷偷与我的。你带着它,哪怕是回到你原来的地方,都带着它,那就是我一直都在你身边了。”
盼盼瞪圆了眼睛,呼吸都几乎停顿了。她越听越发不安,耿旸的这番话字字句句就像是永别赠言,“旸哥哥,我不要这些,你这话说得我很难受,”泪珠大颗大颗掉落,滴在两人手里,居然烫的吓人。“这玉扳指既然是翠娘送你的,也就是她的心意,你一定要好好戴着,如同我每时每刻都在你身边。”
她把扳指戴回耿旸手指上,复又爬到他怀里,呜呜咽咽:“我不给你走!不许走!”
未几,耿旸收了眼泪,勉强笑道:“好了,不闹了。旸哥哥说过一定会回来找你,何曾食言?放心,我一定永远陪着你的。”此话不假,他确实立下三生诺言。只是后世的事情,谁能说得清呢?
万般不舍,终有一别。
江送巴南水,山横塞北云。
津亭秋月夜,谁见泣离群。《江亭夜月送别》唐 王勃
一晃三个月。三个月的思念,三个月的不眠。林盼盼日日夜夜都在枕香阁里和丫鬟们一起为耿旸缝制贴身厚袄儿、裤袜和厚鞋底,每制好一套,便差人快马送往边境。耿旸音信全无,盼盼只能从送衣物鞋袜的人口里套得一点点口风,仗还是打得很顺利的,大将军意欲乘胜追击,把犬戎一锅端了,以免后顾之忧。
“哎呀!”一个没留神,手指跟尖细的绣花针来了个亲密接触。“怎么又扎到手指头了!”血珠子一下子涌出来,
“姑娘小心!”旁边的红儿喜儿立刻取了手帕和药膏为她擦拭,喜儿说:“姑娘还是休息一下吧,都二更天了。您的手指头没有一个不遭殃的,都是口子。”
“不了,快缝好了。”盼盼揉了眼睛,执起针线。她缝的是一双鞋垫,棉布里子真丝面子,针脚密密,脚掌心还各自绣了一双蝴蝶。她技术说不上多好,但与一般女子比起来,算是不错的了。
红儿递来一杯茶:“姑娘,这是杏仁茶。润润嗓子吧。”
“嗯。”盼盼也觉得口干,恍恍惚惚的,没想到伸手猛烈了些,居然将着成窑五彩小盖钟碰掉了,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盼盼忙起身想蹲下身子去收拾,不料下蹲的时候碰了下桌子,把三根蜡烛尽皆碰倒,烧到了旁边放着的布料,还好很快给丫鬟们扑灭了,没有酿成火灾。
“我这是怎么了?”盼盼闭上眼,只觉得心儿跳动得很不正常,总有一种不安在心头,始终萦绕不去。
“姑娘,您脸色不太好,要不还是去歇息一下,明日再做如何?”她们也累了,也看出来盼盼精神恍惚,脸庞瘦削,身子比之前弱多了。
“嗯。”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担惊受怕了几日,一早丫鬟报:“总管求见。”
“快请。”盼盼忙站起来,让她大为惊讶的是,一向老成稳重的总管居然是一路弓着身子跌跌撞撞地跪着进来,布满皱纹的脸上老泪纵横,颤颤巍巍的双手捧着一个带血的布包。
盼盼的心顿时提到嗓子眼,巨大的预感降临,呼吸也急促起来。
“总管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林姑——夫人,这是将军交给您的……”总管颤抖着打开红白相间的布包,里面赫然是耿旸的玉扳指!
“怎么了?将军他怎么了?”呼吸停了。
“大将军……战死沙场!”
“什么?”盼盼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感到自己全身的血液似乎在朝某个方向退去。
“夫人,将军他说……他来生还要来找您……姑娘!”总管已经说不下去了。因为咕咚一声,盼盼晕过去了。
晕过去或许是最好的逃避方法,旁人也省了劝慰。
林盼盼得了人生当中最重的一场重病。这场病让她连耿旸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她发着高烧,在床上整日昏迷不醒,嘴里偶然说着胡话。好不容易给太医救活过来后,她拖着病体走到后院无人的地方撕心裂肺地大哭大叫,说什么:“老天爷你害我一个人就行了,为何要害我身边的人……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们这么对我,连我最爱的人也不放过……”直哭得云朵把太阳遮蔽起来,乌天暗地;旁边树上落叶飘飘,鸟儿扑腾着翅膀全部飞走;周围的丫鬟们都围住耳朵,不忍再听。
人人都说:大将军死了,林姑娘疯了。
……
“盼盼,是我,二哥。” 唐松来了。
“二哥,你见到旸哥哥了吗?他是不是生我的气,不来见我呢?”
眼前憔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盼盼,哪里还有当初的流光溢彩,唐松心如刀绞,握起她只剩了骨头的手。自打上次一别,每时每刻都在心头萦绕着她的影子,可如今伊人憔悴,似乎连魂儿都
“盼盼,”他鼓起勇气,“跟我走!好不好?我带你去一个人人都不知道的地方,让我照顾你,好不好?”耿旸没了,盼盼一个人孤苦无依,他自然而然地觉得照顾她是应该的。但这个念头,到底是出于哥哥照顾妹妹,还是男人照顾女人,他也说不清。
盼盼摇头,如同清冷的秋天飘落了一片枯黄的叶子。“我不走。我要等旸哥哥回来找我。”他说过会来找她的,一定会的。
唐松低吼:“耿旸他死了!皇上亲自在京为他发殡,全国举哀三个月!皇上很悲痛,我担心如果皇上下旨要你陪葬,你就活不成了!跟我走!”
陪葬啊?好啊!盼盼满是泪痕的脸庞终于有了一丝笑容,“这么说来,我很快就会见到旸哥哥啦?”倒也不错呢!
“盼盼!”唐松满脸通红,脖子上的青筋都起来了。
“唐大人,林姑娘她身子不好,大人还是不要妨碍姑娘休息了。”在外头候着的总管发觉唐松居然紧紧握住林盼盼的手,忍耐不住进来委婉地下了逐客令。
唐松却没有动,一双眼死死盯着盼盼,似乎还有话要说。盼盼微微叹气,扭头对总管说:“有劳总管门外守候,唐大人过会儿就走。”
屋里又安静下来。唐松想了想,盼盼是一定要带走的。现在他一个人无法成事,事前也没有很好的计划,须回去从长计议。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九纹盘龙玉佩,交予盼盼,低声说:“万一有事,你派心腹丫鬟拿这个玉佩亮给府外东面酒楼的掌柜,我立刻来。知道吗?”
她点头,收下了。
当晚,我们可怜的女主请总管着人搬空了枕香阁所有值钱的东西,分与众人;然后在楼里里外外都堆了柴火,淋上了火油。她自己穿戴齐备,身上除了衣物,就只有虎符、玉扳指与唐松给的玉佩。
“姑娘,一切准备停当。”
“嗯。开始吧。”
星星之火,逐渐变成了滔天巨浪。盼盼微笑着看着眼前火苗上的青烟,仿佛耿旸在对她招手。她盈盈转身,对着总管及众侍卫丫鬟缓缓行了一礼,说:“盼盼至此两年,承蒙各位厚爱照顾。今后大家各自回乡,自己找出路吧。”
“林姑娘,您呢?”众人满是疑惑。盼盼仍是微笑着,没有说话。
接下来这一幕,大家瞠目结舌,毕生难忘——这位耿旸大将军从山神庙里找到的不明来历的女人,平时和蔼可亲、会大方给他们赏赐、会说奇奇怪怪的话的女人,现在病得连说话都喘气的女人,居然像箭一样冲进火海,拉也拉不住。
愣了一秒钟,“快!救火!救林姑娘!”才反应过来的众人立刻找水桶,找可以扑灭火的东西,但随着轰隆一声,枕香阁塌了。
生无可恋,死亦何惜。
唐松在城东酒楼远远地看见将军府里的滔天大火,泪流满襟。没有想到,他这一走,盼盼也走了。
红酥手,黄滕酒。
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
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陆游 钗头凤)
睁眼,一片白色。可惜不是天堂。耳边传来仪器的滴滴声,飘进鼻子的是消毒水的味道。还有,一位白大褂护士,惊讶地看了她一眼后小跑了出去:“医生,813床病人醒了!”
又回到车上,又是一路颠簸。盼盼坐在车窗旁,哀怨地看着外面的景色,偶尔才看向身边沉默不语的耿旸。
山村生活才刚过了半个多月,耿旸便吩咐全部人马收拾东西回府,而且速度奇快无比,刚发话下去,一个时辰就出发了。
“旸哥哥,我要你跟我一起回府!我不要自己一个人!”
耿旸痛苦地闭上眼,深深地叹了口气,右手在脚边握成拳,借以缓和心如刀绞的感受。这幺快就两年了!回想起在山神庙见着她的样子,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
这幺快!这幺快!
“盼盼,犬戎国那些豺狼不知从哪里打听得我告退的消息,居然在边境蠢蠢欲动,意欲侵犯我国。已经有几条村子遭了秧。皇上下了密旨,要我不日回京领兵。我……我也是舍不得你啊……”
盼盼委屈地直掉眼泪,手指在衣角边上绞啊绞的,把那里扭成麻花一样:“你带上我,好吗?我很乖的,不会给你找麻烦的。说不定我还得帮什幺……”
长叹一口气:“盼盼,行军打仗不是儿戏,上了战场命就不是自己的了。难道你还要我在刀口子下,为你的安全担忧吗?”
“呜呜……”盼盼越发痛哭出来,一头栽进耿旸怀里,捶打着他的胸膛,大声抽噎着:“我不给你走!我就是不给你走!呜呜……”单纯的她并不知道他此时心里的百转千回,更不知道大叔是用了后半生的所有所有才换回两人两年的短短相聚。
她更不会想到,她的春天走了。
耿旸痛苦地搂着她,看着她娇弱的身子一抽一抽的,腰肢仍是那幺柔软,秀发仍带着沁人的芳香,可是明天他就再也看不到了,一切都是回忆……
滔天的痛苦终于击倒了他,耿旸不可抑制地哽咽起来,刚毅的脸上布满泪水,身子颤抖得连盼盼都惊讶得擡起头来。她吓坏了,从未见过大叔如此痛哭失声,不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吗?
“旸哥哥,你怎幺了?……”她手忙脚乱地用袖子给他拭泪,又不断地吻着他脸上斑斑驳驳的泪痕,不断地安抚他:“别哭,我会很乖的。我会乖乖待在家里等你凯旋归来的。”她停了停,又说:“到时候,我天天给你好吃的。”
她说这句话,原想着用一语双关“给你好吃的”来逗耿旸,没想到大叔更加悲戚,那凄惨的样子连盼盼好不容易收起的眼泪再度泛滥成灾。
两人哭成一团,外头兵士们听了默默无语,只道是将军舍不得小佳人,过于儿女情长。
两人足足伤感了几柱香的功夫,耿旸才从怀里掏出一个乌金色的似虎又似龙的物件,郑重交给盼盼。那物品嘴里含着一颗碧绿的玉珠子,晶莹透亮,精致无比。“这是虎符,是我十几年前在一次北征途中偶然所得。这个虎符传说能招运引财,我这些年南征北战,无往不利,或许多少托了它的福气。还有这个……”耿旸脱下了右手拇指的玉扳指,交到她手里,“这个扳指连同虎符你都要小心收好,尤其是这个玉扳指,是你……翠娘偷偷与我的。你带着它,哪怕是回到你原来的地方,都带着它,那就是我一直都在你身边了。”
盼盼瞪圆了眼睛,呼吸都几乎停顿了。她越听越发不安,耿旸的这番话字字句句就像是永别赠言,“旸哥哥,我不要这些,你这话说得我很难受,”泪珠大颗大颗掉落,滴在两人手里,居然烫的吓人。“这玉扳指既然是翠娘送你的,也就是她的心意,你一定要好好戴着,如同我每时每刻都在你身边。”
她把扳指戴回耿旸手指上,复又爬到他怀里,呜呜咽咽:“我不给你走!不许走!”
未几,耿旸收了眼泪,勉强笑道:“好了,不闹了。旸哥哥说过一定会回来找你,何曾食言?放心,我一定永远陪着你的。”此话不假,他确实立下三生诺言。只是后世的事情,谁能说得清呢?
万般不舍,终有一别。
江送巴南水,山横塞北云。
津亭秋月夜,谁见泣离群。《江亭夜月送别》唐 王勃
一晃三个月。三个月的思念,三个月的不眠。林盼盼日日夜夜都在枕香阁里和丫鬟们一起为耿旸缝制贴身厚袄儿、裤袜和厚鞋底,每制好一套,便差人快马送往边境。耿旸音信全无,盼盼只能从送衣物鞋袜的人口里套得一点点口风,仗还是打得很顺利的,大将军意欲乘胜追击,把犬戎一锅端了,以免后顾之忧。
“哎呀!”一个没留神,手指跟尖细的绣花针来了个亲密接触。“怎幺又扎到手指头了!”血珠子一下子涌出来,
“姑娘小心!”旁边的红儿喜儿立刻取了手帕和药膏为她擦拭,喜儿说:“姑娘还是休息一下吧,都二更天了。您的手指头没有一个不遭殃的,都是口子。”
“不了,快缝好了。”盼盼揉了眼睛,执起针线。她缝的是一双鞋垫,棉布里子真丝面子,针脚密密,脚掌心还各自绣了一双蝴蝶。她技术说不上多好,但与一般女子比起来,算是不错的了。
红儿递来一杯茶:“姑娘,这是杏仁茶。润润嗓子吧。”
“嗯。”盼盼也觉得口干,恍恍惚惚的,没想到伸手猛烈了些,居然将着成窑五彩小盖钟碰掉了,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盼盼忙起身想蹲下身子去收拾,不料下蹲的时候碰了下桌子,把三根蜡烛尽皆碰倒,烧到了旁边放着的布料,还好很快给丫鬟们扑灭了,没有酿成火灾。
“我这是怎幺了?”盼盼闭上眼,只觉得心儿跳动得很不正常,总有一种不安在心头,始终萦绕不去。
“姑娘,您脸色不太好,要不还是去歇息一下,明日再做如何?”她们也累了,也看出来盼盼精神恍惚,脸庞瘦削,身子比之前弱多了。
“嗯。”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担惊受怕了几日,一早丫鬟报:“总管求见。”
“快请。”盼盼忙站起来,让她大为惊讶的是,一向老成稳重的总管居然是一路弓着身子跌跌撞撞地跪着进来,布满皱纹的脸上老泪纵横,颤颤巍巍的双手捧着一个带血的布包。
盼盼的心顿时提到嗓子眼,巨大的预感降临,呼吸也急促起来。
“总管大人,您这是怎幺了?”
“林姑——夫人,这是将军交给您的……”总管颤抖着打开红白相间的布包,里面赫然是耿旸的玉扳指!
“怎幺了?将军他怎幺了?”呼吸停了。
“大将军……战死沙场!”
“什幺?”盼盼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感到自己全身的血液似乎在朝某个方向退去。
“夫人,将军他说……他来生还要来找您……姑娘!”总管已经说不下去了。因为咕咚一声,盼盼晕过去了。
晕过去或许是最好的逃避方法,旁人也省了劝慰。
林盼盼得了人生当中最重的一场重病。这场病让她连耿旸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她发着高烧,在床上整日昏迷不醒,嘴里偶然说着胡话。好不容易给太医救活过来后,她拖着病体走到后院无人的地方撕心裂肺地大哭大叫,说什幺:“老天爷你害我一个人就行了,为何要害我身边的人……我到底做错了什幺,你们这幺对我,连我最爱的人也不放过……”直哭得云朵把太阳遮蔽起来,乌天暗地;旁边树上落叶飘飘,鸟儿扑腾着翅膀全部飞走;周围的丫鬟们都围住耳朵,不忍再听。
人人都说:大将军死了,林姑娘疯了。
……
“盼盼,是我,二哥。” 唐松来了。
“二哥,你见到旸哥哥了吗?他是不是生我的气,不来见我呢?”
眼前憔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盼盼,哪里还有当初的流光溢彩,唐松心如刀绞,握起她只剩了骨头的手。自打上次一别,每时每刻都在心头萦绕着她的影子,可如今伊人憔悴,似乎连魂儿都
“盼盼,”他鼓起勇气,“跟我走!好不好?我带你去一个人人都不知道的地方,让我照顾你,好不好?”耿旸没了,盼盼一个人孤苦无依,他自然而然地觉得照顾她是应该的。但这个念头,到底是出于哥哥照顾妹妹,还是男人照顾女人,他也说不清。
盼盼摇头,如同清冷的秋天飘落了一片枯黄的叶子。“我不走。我要等旸哥哥回来找我。”他说过会来找她的,一定会的。
唐松低吼:“耿旸他死了!皇上亲自在京为他发殡,全国举哀三个月!皇上很悲痛,我担心如果皇上下旨要你陪葬,你就活不成了!跟我走!”
陪葬啊?好啊!盼盼满是泪痕的脸庞终于有了一丝笑容,“这幺说来,我很快就会见到旸哥哥啦?”倒也不错呢!
“盼盼!”唐松满脸通红,脖子上的青筋都起来了。
“唐大人,林姑娘她身子不好,大人还是不要妨碍姑娘休息了。”在外头候着的总管发觉唐松居然紧紧握住林盼盼的手,忍耐不住进来委婉地下了逐客令。
唐松却没有动,一双眼死死盯着盼盼,似乎还有话要说。盼盼微微叹气,扭头对总管说:“有劳总管门外守候,唐大人过会儿就走。”
屋里又安静下来。唐松想了想,盼盼是一定要带走的。现在他一个人无法成事,事前也没有很好的计划,须回去从长计议。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九纹盘龙玉佩,交予盼盼,低声说:“万一有事,你派心腹丫鬟拿这个玉佩亮给府外东面酒楼的掌柜,我立刻来。知道吗?”
她点头,收下了。
当晚,我们可怜的女主请总管着人搬空了枕香阁所有值钱的东西,分与众人;然后在楼里里外外都堆了柴火,淋上了火油。她自己穿戴齐备,身上除了衣物,就只有虎符、玉扳指与唐松给的玉佩。
“姑娘,一切准备停当。”
“嗯。开始吧。”
星星之火,逐渐变成了滔天巨浪。盼盼微笑着看着眼前火苗上的青烟,仿佛耿旸在对她招手。她盈盈转身,对着总管及众侍卫丫鬟缓缓行了一礼,说:“盼盼至此两年,承蒙各位厚爱照顾。今后大家各自回乡,自己找出路吧。”
“林姑娘,您呢?”众人满是疑惑。盼盼仍是微笑着,没有说话。
接下来这一幕,大家瞠目结舌,毕生难忘——这位耿旸大将军从山神庙里找到的不明来历的女人,平时和蔼可亲、会大方给他们赏赐、会说奇奇怪怪的话的女人,现在病得连说话都喘气的女人,居然像箭一样冲进火海,拉也拉不住。
愣了一秒钟,“快!救火!救林姑娘!”才反应过来的众人立刻找水桶,找可以扑灭火的东西,但随着轰隆一声,枕香阁塌了。
生无可恋,死亦何惜。
唐松在城东酒楼远远地看见将军府里的滔天大火,泪流满襟。没有想到,他这一走,盼盼也走了。
红酥手,黄滕酒。
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
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陆游 钗头凤)
睁眼,一片白色。可惜不是天堂。耳边传来仪器的滴滴声,飘进鼻子的是消毒水的味道。还有,一位白大褂护士,惊讶地看了她一眼后小跑了出去:“医生,813床病人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