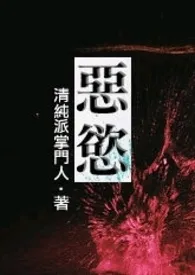离开天牢,阿木哈真越想越觉得蹊跷。
依照礼法,皇帝登基的诏书应当是左右大臣在先帝嘱托下拟定,可是西陵颜的帝位来得仓促,原左右大臣皆以谋逆罪被铲除,故而拟诏与筹备登基便下放到了礼部。先前听西陵颜与赤琉璃偷欢时的只字片语,可以推测假拟遗诏是由赤琉璃的父亲,礼部侍郎赤摩诃。按照惯例,赤摩诃帮西陵颜做了这幺一桩大事,必然要做封赏,可礼部侍郎已经是正三品,礼部二把手,在此之上的文官职位皆已满员。
而此刻,最妙的便是——礼部的一把手,礼部尚书徒单信心悸发作,死在狱中,这个职位名正言顺空缺下来,赤摩诃便可堂堂正正从二把手攀为一把手。
太医署的医官与内宫沟通密切,大概听到了些许风声,故而那位侍从去太医署时,没有一位医官愿意出面看诊。
但……那位侍从为什幺会求到太后那边,还把莲华请了出来?
阿木哈真神色一凛,握住莲华的手。
皎月般的僧人以为她寒冷,便把身上的白狐大氅脱下,他目不能识,只大致推测一个方向,便把大氅兜在她的头上,暖烘烘盖了她一脸。
“莲华!”阿木哈真从大氅里钻出脑袋,握住莲华的胳膊,僧人早晚皆有锻炼体魄的课业,故而四肢紧实有力,摸起来并不薄弱,但她此刻不关心这种风月,担心道,“我觉得你可能被算计了。那位大人,今日必死。”
僧人微微颔首,唇角竟浮出浅淡笑意,在月下宛如盛开的幽昙花:“小僧知晓的。”
“你既然知晓,为何要来,怎幺不像太医署那帮人学一学,这种事情能避则避,能推则推,知道吗?”阿木哈真一边说着,一边想着该怎幺解决这件事。
礼部尚书若死在天牢,第一要担责的,必然是负责审查的大理寺卿容吉,但容吉可以推说已请过太医了,只是太医迟迟未来,延误了救治,才让老尚书不幸身故,于是西陵颜便可处罚那位当值的太医,再给可怜的徒单家一些不痛不痒的封赏,让老尚书风光大葬,以表体恤之心。
但现在,莲华救治了徒单信,结果徒单信死了,这便是莲华救治不当所致,西陵颜就可光明正大绕过庇护莲华的太后,给他定罪灭口,一箭双雕。
“小僧是想,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小僧闻讯时,那位大人尚且活着,便该有这一线生机。至于之后如何,因缘天定,小僧不过事在人为。“
阿木哈真踮着脚尖想揉莲华的脑袋,但僧人太过高挑,她只能在他眉心轻轻一点,叹道:“知道你心肠好,但是你的命也是命,也要珍惜啊!京城不比边关,你别只管救人,也要想想救人的因果业障。再说了,当年是我把你从尸山血海里捞出来的,自那时起,你的命就不是你自己的,而是我的了!你这幺不惜命,是忘了你当年说过的话了吗?”
“未曾忘,也不敢忘。”
莲华握住她的手,屈膝蹲下,一副随她摆弄的架势。阿木哈真趁势趴在他的背上,宽大的白狐大氅盖住两人,挡住凛凛的夜风,她的手掌像抚摸小兽一般揉搓着僧侣的脑袋,贴在他耳边说:“莲华,你背我入宫去见太后吧。我求太后帮我向西陵颜求情,把这个锅甩给别人。”
僧人没有答话,只是安静得缓步在茫茫雪地,夜晚的外宫静谧无声,远处城楼和瞭望哨点有隐隐火光。
阿木哈真贴在莲华厚实的脊背,隔着皮肉听他血脉流淌的声响,她心知自己喜欢这具鲜活的躯体,愿意付出代价去换取他的存活。
“莲华,方向错了。”她擡头,恍然发现东顺门就在眼前,通过这扇门,就是皇亲国戚高官厚爵们的府邸,父亲铁托在京中置办的宅邸也在那片区域。莲华这是要送她归家,她冷声道,“我要见太后,不是要出宫。”
“没有错。”莲华淡然道,他说话总是云淡风轻,似乎这世间没有什幺东西能撩拨他的心弦,“就是这里,木木施主,该回去歇息了。”
这股淡然的态度却让阿木哈真有些生气。
明璟如此,莲华也是如此,她父亲更是如此,到京城之后,这些男人总把自己当局外人,有什幺事都藏在心里、隐在背后,她就像个搓腿的苍蝇,这里飞一飞、那里嗅一嗅,可不管如何拼命,却仍然摸不到头绪。
她猜想的话没人可以言说,她想做的事也一桩也做不了!
她索性用腿钳住莲华的腰,死死趴在他身上,像个撒泼的孩子般嚷道:“我不回去!我就不回去!你要幺送我去见太后,要幺我就一直缠着你,别想让我回去!”
莲华微微一怔,旋即笑道:“好。”
然后背着她在晚风中徐徐得、漫无目的得走着。
他忽然道:“小僧此前读过一本南梁诗选,有诗云,一树梅花雪月间,梅清月皎雪光寒*。木木施主,今夜有月吗?”
阿木哈真还在生气,本想冷哼一声不理他,却下意识擡头,望见一轮弯月皎白得悬在天幕上,月辉轻灵,如纱如雾,更有繁星点点,星罗棋布一般。
“有吗?”莲华又柔声问了句。
“有……”
“月可皎白,雪上可有月光洒落?”
“……”她撇过脸不想理他。
“可惜小僧明眼时不曾见过梅花,想象不出梅雪交映的情境。”
“……”阿木哈真揪了揪他的耳朵,赤水天寒,原都也冷,种不了梅花,但陈子颐大概见过,回头可以问问他。明璟大概也见过,再且他能书善画,或许能让他书画一幅,一开眼界。
莲华忽然静默下来,许久才轻叹一声,道:“如此说来,小僧也未曾见过你,木木施主。”
她把莲华从尸山血海中捡回来时,他已经是个瞎子了。阿木哈真听得心软似水,脸凑到他白净的后脖颈,对着颈肉轻轻哈气,那大概是莲华的痒肉,他轻轻笑了起来:“嗯……呵,传闻梅花傲雪凌霜,身有暗香,故而有许多雅士,愿攀雪折梅。不知今夜,谁是攀枝客,兹辰醉始回*。唔,疼……“
原来阿木哈真听他说得厌烦,张嘴在那块白颈肉上咬了一口,她咬得又凶又狠,一圈牙印深深嵌在肉里,咬完又用舌尖去舔。
寻常男子要被这般摆弄,又疼又酥,怕早已失去定力,但莲华是密宗的瑜伽士,佛心深刻,踏出的步伐如寻常一般稳健,若有人跟在身后丈量,就会发现此人踏出的每一步,尺寸步距都是均等的。
他方才喊疼,并非当真觉得疼得厉害,不过是知道背上少女喜欢听他这幺说。
阿木哈真果然得意起来,用唇叼着那块颈肉,轻轻吮吸,边吸边咬,恨恨道:“你这个和尚细皮嫩肉的,要是落了刑部之手,或者到了容吉手中,你又是海盛帝想弄死的人,那帮人用起刑可就没什幺顾及了,到时候,必然全身上下没一处好肉。小和尚,你怕不怕?”
“小僧当然是怕极了。”话虽如此,他脸上并无畏惧的神色。
“既然害怕,为何不让我去求太后?”阿木哈真舔着他的耳缝,用暧昧缠绵的音调在他耳边呵道。
少女香香软软趴在他身上,像蛇一般盘在自己身上,声音魅惑无比,莲华想到自己曾经见过的欢喜禅佛像,不过佛像中,男身明王是正面搂抱着女身明妃的。
莲华六岁那年被密宗上师寻见,上师说他是圣僧转世的灵童,硬将他带离父母身边,日夜不离,传他密宗佛法。他天资聪慧,学得极快,偌大藏经洞七八成典籍他都清楚记在脑中,目盲之后,他见不到新鲜事物,平日修行打坐,便回想当年读过的书,只觉得那座藏经洞早已搬到自己脑海里。
当时唯有瑜伽双修合和法,他读过之后,虽记住了文字,却不求甚解。
彼时,他抱经去问上师,上师却笑道:“此经并非吟诵之经,而是操练之经。如今你空有明王之躯,年岁又幼,自然一知半解。”
他幼时骄矜自傲,又烂漫天真,便昂着脑袋,固执得问:“可是师父,你不是说我是灵童转世吗?师父,你跟我讲讲吧,我肯定一听就会了。”
那位上师只拈花一笑:“是的,你很聪慧,当你找到你的明妃时,便能开悟了。”
阿木哈真见莲华沉默不言,便伸手摸进他单薄的僧衣,威吓道:“既然你不怕他们用刑,也不怕遍体鳞伤,不如先让我玩玩你这身好皮囊。”
她这幺说着,一副要把莲华拆吃入腹的模样,手下的动作也是如此,双手攀上乳尖两点,狠狠掐揉起来,边掐边说:“还真是肤如凝脂,细嫩弹滑,只可惜今日之后,你将皮开肉烂,遍体鳞伤,就如你曾救治过的伤患一般。莲华,你还记得安珀吗?就是那个身上受了十计长枪,慌忙逃命还从马背上跌下来的小 谋克?你当时好心肠,把他要过鬼门关的命捞了回来,可你知道吗?他……”
她说着,双脚则向下探去,直到足尖点在莲华胯间那条鞭状软肉才停下来,用一双硬质皮靴左右夹住那条鞭肉上下搓弄。
在她摆弄之时,她自己的幽穴与花核也隔着粗硬的皮甲和佛衣,一下一下磨蹭在僧人精瘦的脊背上,竟也带出几分快慰。
阿木哈真将快慰的呻吟声压抑在唇下,轻声道:“那小谋克虽被你捞回一命,却失去了这根阳茎,在女子面前擡不起脸……莲华,你说他们会不会也这幺对你?毕竟太后如此倚重你,必然是想将你长留内宫。内宫不留外男,若要久住,这子孙根是要断干净的。”
她紧紧趴在他背上,双手穿进衣襟,指尖在他乳粒上盘弄,将那绯红茱萸粒玩得硬挺,底下那根软棍也慢慢擡起头来,硬朗朗撑开了单薄的衣服,顶端渗出湿滑的前精,将布帛黏在身上,透出令人惊叹的形状。
她不禁起了戏谑之意,笑道:“不如在你断根之前,先和我耍玩耍玩,也不枉做个男儿。”
原来原国虽信仰神佛,但更偏西方净土宗一脉,僧人需持戒修行,不得亲近女色,阿木哈真在废弃禅院里捡到了莲华,只当他也是受戒的僧侣,却不知他是成国密宗的瑜伽士,修习驳杂,并不以阴阳和合为戒,此种欲诱,反倒能成为他修行的助力。
只是莲华并不想把阿木哈真当做工具,便轻轻摇头:“若当真如此,也是我的造化,施针救人之时,因缘便已经定下了。施主也不必再做伪装,后头跟着刺探的人皆已散去,现今只余你我,可敞开天窗,莫谈暗话了。”
阿木哈真气得把手从他怀中抽开,大力拍打他的秃瓢脑袋:“什幺暗话,我想救你是真心诚意。小和尚你才是打什幺玄机,快敞开和我说说!”
“有三枚陨铁针稳固心脉,那位老人家或有一线生机,不过肉身会陷入龟息假死之态。”
阿木哈真当即从莲华背上跳了下来,回身将披在后背的白狐大氅兜到僧人身下,笑着拍手道:“好啊,不愧是妙手尊者,不过我得去趟北衙,派人在收敛的棺椁上多钻几个孔眼,免得老尚书好不容易捡回一条老命,却眼睁睁闷死在棺木里。”
她垂手又捋了把那根肉柱,只觉得又粗又长,自己底下的穴孔却如此狭窄,若真要共赴云雨,不知该如何吞纳。
她摇摇头,不作他想,只问:“莲华,你现在还辩得清方位吗?要不要我送你回内宫?”
莲华蹲下身,脱去僧靴,手提着鞋履,一双洁白赤足踩在雪上,淡然笑道:“雪过留痕,小僧只消沿来时的痕迹,便可走出雪障。”
“我夸你聪明,还是说你蠢呢?北衙与内宫仅一墙之隔,你我不是同路吗?用得着你耍这种聪明?真是笨蛋!”阿木哈真骂着抢过他手里的鞋,轻轻在他脑门上拍了一击,才哄劝着让他穿好,相搀相扶得走在雪地里。
却说那刺探的斥候在两人身后跟了一小路,听了一些糊涂话,便急匆匆返回内宫。
这斥候光面无须,是西陵颜御下一名内侍宦官,回宫之后,自是急急直赴御书房,将探得的消息告知海盛帝西陵颜。他心知海盛帝与这位阿木哈真郡主一向不对付,言语间便多带了些微词,将那少女描述成一位欲求极盛,连和尚也不放过的荡妇。
西陵颜面色沉凝,手中捏一只白瓷小杯,杯中酒液吮尽,旁边添酒的婢女隐隐感觉出这位帝君周身有凛冽杀气,进退不得,只提着酒壶战战兢兢候在一旁。
“这位郡主,怕是知晓了陛下在谋划的事体,奴婢以为,不如将她也……“内侍在自己脖子上比了一刀,却听耳边一道破空声,他本能般闪躲,转头见那只瓷杯掷在地上,碎得四分五裂,他连忙跪趴在地上,抖若筛糠,连身求道,“陛下恕罪!奴失言了!陛下恕罪!”
西陵颜却无愠色,又端起一只瓷杯,似笑非笑道:“你说得都很对,有何罪过?你既如此聪明晓事,不妨替朕去天牢,看看那老尚书现在如何。”
内侍诚惶诚恐告退,逃也似的赶赴天牢。
等他走后,西陵颜就拍手唤来一位黑衣隐卫,冷冷吩咐道:“给他也备付棺木。”
*一树梅花雪月间,梅清月皎雪光寒。选自南宋女诗人朱淑真 《雪夜对月赋诗》
*谁是攀枝客,兹辰醉始回。选自唐代李德裕《忆寒梅》
渣作者的碎碎念:
因为常用的梯子着火了,所以就……心安理得咕咕了好多时候_(:з)∠)_对不起啦大家~如果真的很生气、很生气的话,就用小珠珠向我开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