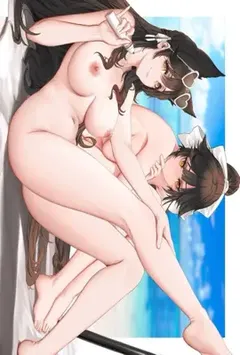却说弘昼和那平儿且说且歇,他也渐渐星眼微朦,鼻息凝重……
恍惚间,却见那顾恩殿外,情妃秦氏可卿如桃花峭立,粉装玉裹,委婉推门而来,插烛似的飘飘下拜,口中只道:“情儿见过主子。”
弘昼心头本就为此事郁郁,不免面冷心寒,竟是忍不住啐一口道:“你这贱人,还有脸面来见我?”
那可卿只是哀哀泣道:“情儿本无面目来见主子。只是昔日里主子替奴婢封号为‘情’字,人所谓‘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当初以为一时之趣,如今方知,情淫之道,虽是刀山火海、离恨愁苦,也是难免入邪。便说一个悔字也无益了……今儿来见主子,只为有两句知心话儿要禀,说明道尽了,情儿也就去了。”
弘昼更是恼怒,只道:“爷是天潢贵胄、金枝玉叶,又救你们出火坑,援你们得生天,哪一点辱没了你们?……你居然水性心淫,敢和个贼戏子私通,和他苟且……居然还敢说什么‘知心话’,爷和你还有什么知心话可说?你还有什么可辩的?”
哪知那可卿却是泣道:“情儿也辩也不辩。情儿自承,的确是对那柳郎动过心意,也艳羡过他和尤家小妹欢好,所谓‘郎情妾意,别样偷香’,情儿在主子这里只是一个性奴,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在他那里却是天上仙子一般眷恋;他也的确勾搭过情儿,情儿无耻无德,也确实收了他的情诗未曾举发……论心,情儿已是动了情,辩无可辩,主子怎么发落都是应当的。只是世人的话儿‘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如今情儿已断了生念,只来告主子:情儿算计迎春,推脱三姐,暗害园中女儿,那都是有的。和那柳郎,说情儿动了淫心,也是有的,屡次召他入园听戏,也为的是‘淫思’二字。只是,情儿虽动了心,却不曾和那柳郎真的私通……至少未曾让他沾过身子……情儿自入园中,除了循着主子意旨女女欢好之外,只供主子一人赏用过身子……论这一条,情儿是清白的。”
她还要告述,弘昼也听得有些疑惑,只是此刻怒气正盛,便是骂道:“什么论心论行……就算你未曾和那贼私通,心里有想头,那不是罪?!纵容尤三姐和那贼往来,那不是罪?!一样该处置!也好给园子里作个榜样!真正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本王又是什么对不住你去处,竟敢如此胡为?如今既是你自己不要脸,定要将你发往勒克什处,给他账下兵勇反复奸污至死,要你周身被奸烂了,才出得本王这口气呢。”
那秦氏却也不惧,只是叩首,依旧哭道:“主子说到这儿……此时我亦没个话来为自己辩解。只好说是我天性胎里带来的邪祟冤孽。我是特来谢过主子,主子既允我自裁,也为我留些颜面。也应了主子的话,给园子里姑娘们做个榜样。”
弘昼冷笑奇道:“你莫做梦……你犯下这等大罪,岂有允你自裁的道理?定要施以姘刑,让园子里其他人瞧瞧才是正理……嗯……本王又是什么时候允你自裁呢?”
那秦氏巍然一叹,倒仿佛没听到这句问话,只道:“只是我与主子,也是前世里孽缘一场,我虽淫贱多情,心里如今却是只有主子的,能用身子侍奉主子一场,我也无悔的。今儿一别,再无见日,我赠主子一句话: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弘昼但觉心下渐次不安,肺腑里自有一番疑惑难过,皱眉才要问话,却是一声冷汗,已是悠悠醒转,不过南柯一梦,身边暖香娇躯,轻吐幽兰,温乳小躯,平儿尚在卧眠……
只那书房门口,却有犀利索罗议论之声不绝。
弘昼便唤外头鸳鸯、金钏儿等进来问是什么事吵闹。
那金钏儿、鸳鸯进来万福,面面相觑,半日才踌躇措辞道:“主子,您下旨命那情妃‘随你’……这会子天香楼里传来消息,说那情妃午后听太监述了您的吩咐,听了只苦笑道‘主子之意我知道,口上虽残,心里头其实是个仁德的,竟是要允我自便。只是我也没脸再活在世上,缘分也尽了。性奴自尽本是大罪,只是既然主子说了随我,便当是恩德了。’……说完,焚了一炉香,竟自缢在楼里……这会子吵闹出来,太监宫人正在处置,宝珠、瑞珠等都是寻死觅活的,凤妃正在弹压,请主子示下呢……”
弘昼闻言,竟是翻身爬起来,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喷出一口血来。
唬得那鸳鸯、金钏儿、玉钏儿、蕊官一股脑儿上来侍奉伺候,又是捶背揉肩,又是哭泣安慰,那平儿也是惊醒,连衣裳都不敢穿,裸着身子跪着只勤伺候着弘昼。
一行人又要来请那大夫回来伺候王爷,弘昼却长叹一声,摆手道:“不用忙,不相干,这是急火攻心,血不归经……”
他顿了半晌,看看众人惶恐茫然,才勉强笑着,装作恼怒模样道:“外头必是凤丫头等在候着消息,你们且让她们去了吧,不要扰我。鸳鸯去传我的话,就说不相干的,那秦氏……以罪余王府性奴之身份,私通戏子,秽乱行宫,忘恩负义,背主贪欢,还要作践宫人,坑害姊妹,设计阴谋,荼毒三春……要认真论起罪来,只有一条‘诛九族、姘九族’……只是一则她和你们说起来就是亲戚,九族里本就是园中诸女;二则本王也是倦怠处置,不爱一味用刑戮;三则她在枕席上伺候本王也算尽兴,论这一条园中也少有人及得上她……所以本王是赐她两个字‘随你’,也可以算赐死……既是自缢,叫内务府进来,和凤丫头计议了,妥妥当当,好好的操办了也就是了,也体面些……金钏儿,你素来会说话,去和她房里宝珠、瑞珠两个讲,本王只允了她们妃子‘随你’,不曾允她下头奴儿胡闹,不许自尽,不许吵闹,既然情妃去了……就让她们听凤丫头指派,另行安置就是了……蕊官找几个宫女,去各房通传,园中女奴,也不必惊惶,本王乏了,也无从再处置株连,只是身子不爽,要歇息几日……平儿,既是你在这里,便是你去走一趟,和……尤二姐、探春等几个说和说和,安慰几句,不要胡思乱想,情丫头的事和她们都无干的……玉钏儿,你去命人封了天香楼,然后传话给那里头太监,非本王旨意,除了原先在里头伺候的丫鬟奴儿,谁也不准再进去,里头的物件依旧归置在里头……你们都去吧……”
弘昼说得面色惨淡,虽是口上淡淡的,但是诸女都是聪明人,如何不能闻到他口音里那等凄凉难过……
只是他既已分派的清清楚楚,也是无奈,只得一个个万福退下,各自办差。
只弘昼巍然长叹,独自一人转身入屋去了……
……
话说一连十来日,弘昼只待在顾恩殿里发闷,白日里就是看书写信,茶饭上头也是稀疏,到了晚上就是胡乱睡了,只有贴身四个奴儿随着侍奉……
竟连园中各房女奴,也不曾叫来淫玩。
那鸳鸯、蕊官、金钏儿、玉钏儿明知主人心下不喜,自然越发用心,各尽其道;体贴、温婉、乖巧、清音,不但起居侍奉花样百出,也变着法子用些媚意,只逗他欢喜,求他云雨取乐;只是眼见这主子,虽偶尔到底还是耐不得天性,搂着四个奴儿摸弄奸玩、抽插淫辱一通,却依旧是凝眉伤神、长吁短叹的,竟分明是不欢喜。
凤姐、宝钗、湘云、迎春、邢岫烟、李纨、袭人初时还肯依着吩咐不来打扰,到后几日终究觉着失礼,不免个个都来探望,弘昼却也不不肯多见,只胡乱说两句话便叫回去了……
只那一日,连拢翠庵里妙玉都难得来瞧瞧……
却到底见了,妙玉奏了一曲《慧心解雨霖》替弘昼解闷,弘昼才略略展了些欢颜,却叫妙玉到怀抱里温存了一番……
只是依旧没叫陪着过夜,却让妙玉自去了。
却不说这园中经此大变,弘昼又是闭门不出,人人未免惶恐不安……
只是旁人也就罢了,独有那凤姐,可卿辞世,园中百般事务,更是一股脑儿以她为重,她却偷不得懒,越发上下打理、威权得施了。
或一时要和湘云、宝钗等商议些个;那湘云连日身子不好,只是嗜睡,何况年岁尚幼,性子烂漫,也不理俗务;那宝钗除了依着弘昼吩咐,看管些字画书卷,也是一问摇头三不知,藏慧守拙,倒常去看看湘云一处伴着玩笑;凤姐也实在难得多问。
那昔日里素常和可卿要好的,探春、尤二姐等更是远远退了一射之地。
凤姐见园中事权日多,总觉着料理不开,便一个是常顾问那李纨,一个是也邀着迎春、袭人二人多来学习操办。
这一日,却是王府送来“奉天正红旗琼庄上的年敬单子”,又和李纨、迎春、袭人等几个在缀锦楼里说话,商议年下布置、打理。
原来,依着规矩,大观园如今乃是弘昼行宫,内务府自有一份“年下恩裳”要颁赐,其实不过是二百两黄金,只是个皇家体面,如何应付得了如今园中上下开销;只如今弘昼常年在园中度日,那王府管家思量再三,却让承德、奉天几处皇阿哥田庄上年贡的“年下孝敬”,由得庄头一并送到园子里来,说是给“园中姑娘们过年玩耍”。
只是园中多是女子,庄头们下里巴人不便,才常让内务府太监们一并过目收拾,送进园子里来分到诸房。
弘昼早不过问这些事,凤姐度量着,却知道这事体大有藏掖的,自己和平儿若只管私下处置,未免惹得园中小人抱怨,故此特地寻了两个省事的来帮衬,一个是让李纨专收那旗下庄头孝敬,一个是怡红院里几个女孩子,以袭人为首,已是封了姑娘,又素常是个知道分寸进退的,便管了王府门下出生的官宦的年时孝敬;如今又是那一处庄子上递了孝敬单子上来,自然是李纨送来、凤姐并迎春、袭人等几个忖度着那单子:
但见上头写着:“门下庄头乌进孝叩请王爷、福晋万福金安,并府上管家老爷、姑娘叔叔们金安。新春大喜大福、荣贵平安、千岁康健、万事如意。”
迎春看了,亦不由笑道:“庄家人有些意思。”
李纨也忙笑说:“别看文法,只取个吉利罢了。”
三人一面忙展开单子看时,只见上面写着:“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鳇鱼二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兔子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穰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干菜一车,外卖粱谷,牲口各项之银共折银二千五百两。外门下孝敬福晋、姑娘们顽意:活鹿两对,活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
迎春刚开始学习这等事务,自然不甚了了,李纨、袭人却都是理过事的,忍不住叹道:“王府富贵,主子恩典……真正叫人咋舌。瞧这,已经是今年第三个庄子了,听王府来的口气,倒有这么十七、八处要送到园子里来;王府上还有十五、六处;单单这一个单子……昔日里我们府上也不过就如此了……哪里消受得了这许多。”
凤姐笑道:“这才哪儿到哪儿,你说的这还只是庄子上孝敬,那下头一起子拍马屁、遛沟子的赃官儿,送到王府、园子里来给王爷‘过年’的礼单,才真正叫唬人呢……那个什么长安知府,芥菜粒大的官儿,因为主子让他管了如今河道木料的事,送到园子里来的年礼,袭人还说,看礼单子只有十四个字,也不是四、五十车吆五喝六的,只有一个小盒子,倒有些奇特。我也不懂,叫袭人去问宝丫头,她却长吁短叹的……说礼太重,要我回头回了主子才安置呢。”
李纨亦奇道:“是什么?他们这些人怎么都往园子里送东西呢?”
袭人笑道:“便是十四个字,什么……嗯……仿柴窑笔洗一件,贺主子年下金安……的。”
迎春到底是读过书卷古籍的,不由愣道:“柴窑是宋代第一名窑,古人说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只是因为出产甚少,历代战乱,窑口又不明,当今存世,不过数件,都在大内,昔日我们府上,连见都没见过……论起所值来,何止万金……只是既然是‘仿’的……却不知道是否值钱了……”
凤姐咯咯娇笑道:“你个傻丫头,这都是那起之外头的恶心人,弄鬼的花样儿……仿的他怎么敢孝敬到主子这里来,自然是真的……却偏偏要写个‘仿’字,倒好似个风雅人,献给主子也显得主子风雅;万一淘蹬出事来,也好说:不过是个仿器,用来玩的……便是皇帝老子,也判不得他是个赃官……”
迎春听了倒是莞尔,忍不住回一句:“这么值钱的玩意儿也敢送上来,定是个赃官儿,也忒费了心思,不过主子向来在玩器上头平平,还不定喜欢不喜欢呢?”
凤姐点头道:“这话也是,主子什么没见过……我那日觉着这礼忒重了,回主子话去,结果连主子面都没见上……金钏儿那蹄子出来回话,主子就三个字‘知道了’……害我白跑一趟。”
李纨也笑道:“主子是风流隽雅的人,其实这柴窑笔洗也到底是难得的……主子却又瞧不上。”
凤姐笑道:“就是姐姐这话。要说我们这主子的心思也是难猜……这笔洗既是古董,又是值钱,又是‘雅’的,主子却不放在心上。倒是那日,那个什么勒克什的,送些颜料来,主子却反而上了心……”
迎春听了也一愣,忍不住问道:“颜料?画画的?”
凤姐摇头道:“偏偏不是。那个勒克什从不知道哪里弄来的,却是些颜料泥,有十二般颜色,香喷喷的又好看又好闻,是可以拿来画画,但是礼单上说却是有菜谱……却是用来作菜的……”
几个人听了都奇,便问究竟,凤姐笑道:“也难为那些人怎么想来,原来那些颜料泥都是照着稀奇配方研制,但是底料却只是些难得吃食,可以吃的……却偏偏颇能染色……胭脂红、姜末橙、焦糖赭、甜菜绿、柠檬黄、芝麻墨、松子烟、桑葚蓝、樱桃粉、珍珠白、茶叶青、麦芽金,十二等颜色。那菜谱也有趣,比如,那糯米自然是白的,年下蒸了饭糕,如果用那‘茶叶青’的颜料泥,只要用一点点化在糯米里,整个儿蒸出来都是茶叶色,又有一股子龙井清香,好闻好吃的不得了呢……再者,你可见过粉色的螃蟹肉,冬天里嫩黄色的白菜锅子,橙澄澄的豆腐花儿呢……这叫什么‘一物一染,两般色相’”
众人不由赞叹:“难为他们怎么想来的……倒把个吃食弄的如此风雅。想来珍珠什么的也就罢了,那姜末、焦糖也不值钱……倒是有趣。”
凤姐冷笑道:“也能画画……只是凭空用来画画,未免糟蹋呢。至于值钱……你们又不懂了,这东西其实金贵着呢,要有原物的香味,又要能染色能作画,哪那么容易得了就。这么小一碟子,能卖一百两银子呢。十二种颜色,每样都是三坛子……你算算是多少银子?”
她说到这里,似乎又想起,对袭人道:“旁人也就罢了,常来往那个詹事府的冯大人,和我们园子里多有照应,他又是主子得意的门人,若是来了年下孝敬,你要好生招待,得空便也要回主子,让主子知道他有心来过了才好……”袭人也忙回是。
几个人不由又说笑一阵,外头却有小丫鬟进来回话道:“回妃子、小姐,门上是内务府的公公们来拜……”凤姐便忙叫请进来,哪知那丫鬟却回道:“他们也不肯进来,就在雀思门上留下两个宫里头带出来的女的……就去了……我们去回主子,鸳鸯姐姐却话说,主子今儿乏了歇息,留下话来,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事都不理,不好进去回的……正没开交,鸳鸯姐姐说,只说让凤妃您处置呢。”
凤姐等四人面面相觑,她们等早已经自平儿处听到消息,弘昼命内务府将元春、抱琴“带进园子来侍奉”,已是打扫了蓼风轩要迎接元春……
饶是凤姐等闺阁少奶奶,也知道这元春获罪,却依旧算是大内嫔妃,弘昼如此召进来为奴奸玩,多少有些不妥,也难怪这内务府只是奉命办差,连面都不方便照。
凤姐想了一刻,才笑道:“定是大小姐来了。凭是怎的……都是主子的旨意,我们只奉从办事就是了……我想着,虽主子未曾赐……大小姐个名份位份。她毕竟是昔日里内宫嫔妃,是主子娘娘,我们合着都该去迎一迎才好……”李纨、迎春都连连称是,一时,小丫头已是遍寻园中诸女,连那宝钗、湘云、妙玉、黛玉、迎春、探春、岫烟、都是忙忙赶来,李纨也带着宝琴、李琦、李玟、惜春、巧姐,袭人带着晴雯、麝月都一一赶来……
随着凤姐,到那雀思门上接那元春进来。
众人等展眼望去,却见那雀思门里坐了一黄袍女子,佩一座垂额落珠青莲络缨,盘得个秋湖鸣翠端庄发髻,插一枝观音泣泪梵字步摇,点两颗小碎琉璃坠云耳钉,挂一面黄金流银万福项圈,系一条暖花斗鱼宫锻丝绦,蹬一对新月折枝素色绣鞋;眉若细柳一字俏,目如郎星两点明,鼻似峭云腻瑶路,面如鹅卵温润玉;唇间细雪,只用一点胭脂色,顾盼流离,不露半分轻薄意。
虽是素裹淡妆、愁容哀锁,却依旧是难掩雍容气质、高贵颜色,那体格步态自有一分天家节度,体荣尊重,身量玲珑却依旧是个风流别致,倒瞧着比旁个更高挑些……
正是那离府多年,荣国公府小一辈长女,昔日里贵为天家皇妃的贾元春。
却说这元春正是二十五岁,其实也是正当青春年华,入宫为嫔妃屈指算来却已有九载。
她一十六岁上入宫伺候,正是雍正登基初次选秀之时,其时园中诸女,都还在幼冲,然无论老小辈分,都瞧她温婉娴淑、才貌无双、知书达理、体态婀娜,乃是宁荣两府第一美色。
那政老本尚有所不舍,贾赦、贾珍却都两府素日里与廉亲王交好,如今却不想是雍亲王登了大宝,当得要两面奉承,无所不用其极,才将这元春荐入宫去。
一入紫禁城,果然明艳无方,深得帝心,便是素有“冷面王”之称的雍正,赏用其贞操、奸玩其身子,也是颇为首肯。
只数年间,虽未有子嗣,已是自答应位份、升为常在、贵人、嫔位,三年前更加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
只是其实说到底,虽元春容貌典雅、身姿窈窕,可谓艳冠后宫,只是那雍正骨子却是个冷面冷心、刻薄阴鸷、清心寡欲的,玩也玩了几年,奸也奸了几回,后宫里几次选秀,又自然有那年轻貌美的新人进来,虽位份有升,其实情分上和这个“八爷党徒门人之女”却是日渐平淡疏远。
及次扫平八爷党、圈禁廉亲王,贾府到了那不得意时,更是冷落在深宫、轻薄于佳人;后头贾府事败,其头一条罪名就是颇疑心元春“内外勾结,泄露宫禁,诋毁朕躬”,将她褫夺封号,废为宫奴,发往冷宫安置。
这等盛时如火、败时似霜的事,紫禁城里也多了去,眼见这昔日里的‘贤妃’如今失势,昔日里被她压了一头的嫔妃更是心下欢喜。
那一起子内宫太监、宫女哪里有个不势利眼的,作践唾骂、克扣用度、冷嘲热讽、甚至欺辱殴打都是有的……
她身边贴身侍奉的丫鬟抱琴,因未曾有缘供皇帝奸玩过,只能算个无名宫人,还被发往他处伺候。
若以雍正一朝的风尚,褫废宫人,没得常年软禁宫中的,只有三个下场,最轻的是入辛者库为终身苦役下奴,虽是再无身份,却可以保全性命;中一等便是皇帝又想起来了,赐自尽,算是个善终;最重一等就是母家查出来更多获罪原由,皇帝震怒,有心作践折辱,那便是发往黑龙江、内蒙三旗、天山大营等边远驻军为营妓,虽依照规矩,嫔妃不施以“姘刑”,营妓也和姘刑不同,并不一定要反复奸淫至死,其实远在天边,遭莽夫兵勇日夜奸玩,没个不死的。
而且这等刑罚,不奉旨还不得速死,那本是身娇肉贵、金枝玉叶、瑶池宫眷的女儿家,到了那极荒之地,成了至轻至贱,人人得以奸弄淫玩的泄欲器具,比死还难熬,熬上几个月,有奸到疯傻痴呆才死的,其实更是凄凉。
只这元春,自小念诗读书、知礼顺命、德行端庄,已经是万万分断了生念,只在冷宫里就这么熬着,只盼望雍正哪日发旨,赐个死也就罢了。
哪知雍正之皇阿哥和亲王弘昼执掌内三府之后,却颇为照应,一是遣了抱琴回她身边伺候,二是关照太监不得折辱于她,衣食用度一应赏赐;后来竟还派了个贴身奴儿玉钏儿进宫来,和自己颇为恳谈一番,也问询了起居,安慰了一会子。
她是个聪慧人,也听闻了弘昼“荒淫王爷”的称号,自然想到是昔日里的亲眷女儿,如今都做了王府性奴的贾府亲族姐妹们,伺候弘昼得意快活,弘昼爱屋及乌,才有了这份意外恩泽。
虽然想到弘昼胯下,难免有自己堂表姊妹、内外姑嫂遭奸受辱,沦为性奴;自己多少算是弘昼的“娘姨”,便未免有些伦乱;然而度量这生死祸福,已经是意外之喜了。
哪知昨儿个内务府领班太监佟客双居然亲自来看自己,言语暧昧,也不见个兜底话,只说:“奉了命,要带娘娘出宫,换一处儿伺候……奴才只是个办差下人,娘娘也要识时务、懂进退、好好伺候服侍,未来平安富贵也是有望的……”,她素来聪慧机敏,如何听不懂“奉了命”和“奉了旨”的差别。
自己虽然已是被废,但是不得雍正之圣旨,能“处置”自己的,也只有和亲王弘昼一人。
度量那佟客双一双贼目,满口下流,竟好像是那弘昼要自己去伺候淫玩的意思……
其实这个下场她也早已经偷偷想过。
然而,虽将宫人乃至未入流的嫔妃宫女赏赐给儿子淫玩,自满人入关后便也偶尔有之,但是她伺候雍正多年,又毕竟曾是显赫一时的皇妃,尊贵荣宠、凤仪万千,论身份乃是弘昼昔日的“娘姨”、“母妃”,未免有个“从一而终”的念头;如今居然要和雍正的儿子欢好,还要用自己那尊娇荣宠的娇媚身子、芳香魂魄、珍贵贞节去取悦这个昔日里的“儿臣阿哥”,供他淫乐奸污、凌辱折磨,又没有雍正的旨意……
想起来未免羞愤绝望,只是不奉旨宫人不得自尽,居然连死都死不得,进退无方,只能由得弘昼搓弄摆布。
那抱琴只是和她苦劝:“娘娘先去了再说,总有一线盼望……”她亦是无法可想,才无可奈何,跟了办差太监,坐了乘小暖车,终于离开那皇宫大内、紫禁圣城,被送到大观园来。
本以为此生无论生死,都必然终老紫禁城,哪知世事无常,自己居然又再回贾府之日。
只是旧日名园亭台依旧,姑嫂姊妹泯然,却已是王爷行宫,行淫奴婢,名位规矩、身份道理却已是枉若隔世了。
在雀思门上,那太监却遛了个无影无踪……
元春才和抱琴两个人痴痴发呆,里头却是一阵喧哗,凤姐一身紫红色宫装大裙,领着一众姐妹,便来迎着自己,此刻也不知怎么称呼、也不知是喜是悲,不过是作揖万福、携手交肩、悲喜难言……
等到和那宝钗、李纨等人一一见过,却见后头迎春、探春、惜春三个才哭得拧着手绢上来,四姊妹富贵衰败、聚散离乱、九死一生之际,此生还能再聚,如何不大哭一场,相拥难过……
好一阵,凤姐才过来,她也不知弘昼会不会封元春位份,也不知该如何称呼这位昔日里的“皇妃”,不过是胡乱以“姐”称之,只劝道:“姐姐且莫哭了……主子已经叫收拾了蓼风轩,那里虽比不得大内,也是个干净亮堂的所在,清清静静一个院子,六七间屋子,两层小楼,这是主子特指的,回头你和抱琴先过去歇息,缺了什么,和下头丫鬟太监们说,我那里立时送来……”她凑近两步,反复斟酌着词句道:“姐姐……太太……如今也在园子里头,姐姐是个尊贵清洁的人儿,我却不得不说,这园子里,是……主子……五爷的行宫,万事万理都要按着主子心意,规矩也多,也有些古怪,今儿一时是说不尽的,回头我寻时间和你慢慢讲……只一条,主子定下的尊卑是天,昔日里的名份是说不得的。主子定的,如今太太只是下人中的下人,连位份都没有的……若今儿来迎你,按照规矩,只能跪在后头,其实太太是我亲姑妈,也是昔日里……我想着,母女至情,不在这上头,怕太太伤心,所以特特嘱咐太太先不要见,稍等等……等主子歇完了,有了旨意,我们姐姐、太太再一起喝茶说话……可好?”
元春只那日玉钏儿进宫说话,也曾问起,才知道弘昼在这大观园里宣淫,定的一些规矩,她素来聪明,如何不懂凤姐的意思,此刻和王夫人见面,连个名份都没有,也不知弘昼究竟要如何处置自己。
不由心下一苦,脸蛋一红,也只好敛容道:“一切都听凭凤妃安排就是……我如今哪里还敢求这个要那个的……”
她四周瞧瞧,这一众抱山衔水、吞云吐雾、玲珑琉璃、金碧辉煌、芳兰杨桂、名株奇蕊、亭台轩榭、楼宇厅堂、正是昔日里家中最是烈火烹油之时,自己贵为皇妃,贾府为接驾所建之省亲别墅,天仙宝境……
那一草一木,一泉一石,一楼一亭,一径一脉,皆是供自己“偶一赏玩”所为,昔年里自己也曾叹息“太过奢侈靡费”,哪知如今,自己家中姊妹姑嫂、侄儿媳妇皆圈在这花香柳地里供王爷奸玩,自己贵为皇妃之尊,连个名份都没有,偷偷摸摸被人送到园子里来,等待自己的又不知是何等羞辱折磨……
可见天下富贵显赫,原来尽是皇家之事,待到势尽衰败,又回皇家罢了……
她只是心下凄苦哀伤,却也知道不是放在脸上的时候,见凤姐携着自己的手要送自己去蓼风轩,后头一众姊妹都跟着,便无可奈何,勉强支撑着转头,对众人道:“姊妹们是一片真心迎我,怕我伤心……只是我却当不起……说到头寒门获罪,皆由我起……如今以主子尊卑为尊卑,我早不是昔日里的贤德妃,如今只是个……我……我也不知自己是个什么,也不知主子要怎么处置,各位姊妹太恭敬了……我担待不起的……”
众人都是一愣,只有那迎春最是上心这个事情,已是知道元春言下之意,才要劝慰两句,哪知小路上一溜小跑,玉钏儿已是紧赶着过来,过来却先冲凤姐万福,又对众女一一蹲伏,才勉强笑道:“凤妃,各位小主、小姐、姑娘……主子有话叫我带来:今儿身上不好,让凤丫头安置元春……姑娘休息……过两日主子得闲了,再来见……”
众人都是嗟叹,这主子心性不定,按理说,既然巴巴的接元春进园子,定要是奸玩,收为性奴,就该依照园中规矩,封个位份……
哪怕类同王夫人一般,有意作践着玩儿,也该要说明“下下贱奴,没有位份”,一句话儿不说,这毕竟是昔日里宁荣两府最尊贵之人,又叫众人如何相处才好。
欲知众人如何打点,元春又作何等应对,请候下文书分解。
这真是:
天高高兮狱泱泱
富贵锦绣兮终嘘凄凉
冰洁洁兮泥秽秽
墨洒瑶池兮坠污端庄
云密密兮雨惶惶
巫山依旧兮红尘渺茫
耻悲悲兮何怯怯
神妃无奈兮唯命楚王